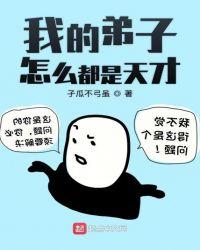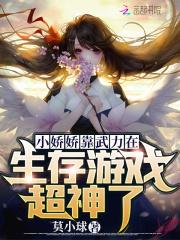笔趣阁>扶苏穿成宋仁宗太子 > 120125(第18页)
120125(第18页)
至于怀疑自家年仅八岁的孩子,有那等心思之事,曹皇后是眼睛也不眨,一点儿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前朝后宫,满朝文武,谁会真正把肃儿当成八岁的小孩?而且《礼记》规定:男女七岁就不同席。八岁,也不早了。
不然,还有什么能解释肃儿远在云州,还要特别来信拜托她呢?难道他真的闲到无聊,宁拆十座庙,也要毁一桩婚吗?
扶苏:我是!我是啊!
如果扶苏知道了几百里之外的曹皇后误会成这样,一定会顿感晴天霹雳,然后对着自己亲娘哀嚎:你们往上数,别数老赵家的,要看就看老嬴家啊!
更何况,他是经历过社会主义洗礼的新时代战士,两辈子的孤寡人士,心中除了大宋和十六州,再无其他!
好在曹皇后也只是停在猜想上。她连自家儿子不想当太子都准允了,怎么会对他的感情生活指手画脚呢?还是让妙悟和那苏家的小姑娘一道相处吧?看两人的性情和谈吐,应该交往起来很合得来才对。
事实也确如曹皇后所预言一般。
苏轸出了坤宁宫,随着妙悟来到了她自己的住处,感觉呼吸也顺畅了许多。一来炭火没那么足,而来就算皇后再平易近人,那也是皇后,寻常人都会感到些压力。
在年龄相仿的妙悟殿下面前,苏轸就觉得自在多了。
何况,她的住处中的陈设,简直让苏轸宛如一只掉进了米缸的老鼠一般:“莫非这是……整整四年的《求知报》么?”
“对呀对呀,是我一期一期攒起来的,你要看吗?”
苏轸如饥似渴地点了点头。
眉山路远,当地书局能力有限,每一期的报纸都要靠抢的,总有苏家来晚了没抢到的时候。她尚未出阁,又不好上人家家里找当家人借阅,每一次都深觉得遗憾。
但她又不愿意为了一份报纸写信麻烦京中的父亲和弟弟。
妙悟:“那你看吧,想看哪期看哪期。”
至于“要爱护”、“别弄丢”之类的话根本不用她嘱咐的。苏家阿姊一看就是极妥帖、极细心的那种人,做不出搞丢之类的事儿。
妙悟给苏轸找了一个光线好,坐着舒服的地界,自己也去看书去了。苏轸未免好奇:“殿下日常都看些什么呢?”
“喏。”妙悟把书封一抬。
“……《齐民要术》?”苏轸十分不解,脑袋上冒出个大大的问号。
比起这本,应该是班昭、长孙皇后她们的著作更符合公主的画风吧?
“你知道我阿弟,也就是太子他弄出来的棉花和土豆吧?”
苏轸点了点头。
这两样东西,在眉山她都见过。不知道让多少人吃饱穿暖,免于饥馁寒冷之苦的。赞颂棉花的《捧雪集》还收录有她阿弟的文章呢。
苏轸忽然意会到了什么:“所以……殿下你也想效仿太子?”
“对啊,要是能从书里头,发现什么崭新的作物啊。农具就好了。”
话说到这里,妙悟看了看左右,忽然凑近了对苏轸细细声音道:“而且,我阿弟跟我说,如果我真的发明出什么了,他就去帮我求阿爹,就是官家,让官家不让我出嫁。”
“……啊?”苏轸手中的报纸掉到了桌上。她飞快地把报纸捡起来,确认没有缺页、折角,爱惜地将之平铺在桌上,方才缓过神来,回应起妙悟大逆不道的话。
“身为女子,怎、怎能不嫁人呢?”
—
“官家,您有事找我?”
另一边,苏轼见官家就没那么拘谨了。一来是他性格开阔之原因,二来君臣四年,彼此又因为扶苏有一定的熟悉,彼此都不陌生。
“朕业已听范卿说了,你凭蛛丝马迹猜出肃儿身在云州。写给他的信,也一齐捎去了。”
苏轼的脸上立刻绽出笑容。
虽然他把信给了范相公,久久没有回音,但既然没有到退回给自己的地步,苏轼于是猜测此事多半是成了。但从官家的手里亲口认证,他还是高兴得不得了。
“谢官家成全!”
“何须言谢?肃儿有你这般牵挂他的挚友,亦是好事一桩。”
仁宗没有说过,他曾忧心肃儿年纪轻轻就通晓世事,未免有慧极必伤的风险。好在大宋朝堂人才济济,也有苏轼般和他相处甚佳的挚友,不至于让儿子太孤寂。
所以,他对苏轼一向十分宽容欣赏,就算知道他勘破了国家机密之一,也未曾提防谨慎,反而愿意把话摊开了说。
“那你可知,肃儿如今在云州是何光景?”
“臣不知,但请官家相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