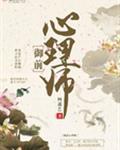笔趣阁>假死后将军火葬场了 > 8090(第15页)
8090(第15页)
并州的葡萄,比起长安的葡萄似乎也不差什么,有区别的是人。
一瞬间,林寓娘想起了很多事,初上长安不通礼仪闹出的笑话,旁人明里暗里的嘲笑,想起晋阳公主指派她伺候,想起她头一回见到的葡萄。
长安,这个地方似乎已经离她很远很远了,从麟游到江城,再从江城到幽州,她已经整整三年不曾再靠近京畿,自然也没再遇到过旧日的那些人。可是长安留在她身上的一切却从未消失过,刻入身体本能的规矩礼仪,鼻间幽幽缠绵不去的香气,甚至就连她的这一身医术,也是长安的楚鹤教授给她的。
三年过去,也不知道老师究竟如何了,还有……
方才在席间听见的一言半语,此时凭空钻进脑海里,挥之不去。
“那位几擒国主的大将军,我记得好像是叫……江铣?后来再没听说过他的消息,也不知是不是战死了。”
离家出族之人,按律不能任官,就算没有死,只怕也……
林寓娘盯着指尖发了好一会儿怔,突然如梦初醒,甩甩脑袋,拍了拍裙摆上的尘土,提着医箱同捧盒进屋里去了。
……
长安,太极殿。
“新罗、高句丽、百济三国原本同为大秦臣属,本该平齐平坐,可是高句丽自恃国强,百济阴险狡诈,与高句丽狼狈为奸,竟强占我国四十多余座城池,占我国土,辱我生民,甚至抢走了原本要献给大秦陛下的百车岁供。我国虽然深陷战乱之中,可女王从不敢忘记大秦恩德,特地派我前来请罪,拖延岁供并非是我新罗有意为之,实则是高句丽与百济两相夹击,我新罗国民已再无立锥之地啊!”
新罗使臣坐在地上涕泗横流,哭得几乎失去了一国使臣的所有风度。但高句丽势强,百济占据地利,夹在中间的新罗国弱民孱,只能受着夹缝气。
派遣使臣前往大秦求援,已是他们的奋力一搏,若是大秦也不肯出兵相援,只怕剩余的城池也再保不住。
新罗使臣涕泪俱下,倒是也引起朝中不少人同情,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不论是否出兵,都该谋定而后动。
皇帝安慰几句,让人把哭得脱力的新罗使臣扶下去,捏了捏眉心。
“玄奖,高句丽怎么说?”
新罗之患,并不是今日才有的,高句丽同百济对于新罗的欺压也不是一两年的事了。早在先前,出使高句丽的使臣毁坏他们用前朝将士尸骨建筑起的京观之后,高句丽便大兴土木,在北境一线修了道长城用以防范大秦兵马。修好长城之后,高句丽便马不停蹄地对新罗与百济发起进攻。百济倒是乖觉,及早向高句丽投诚,高句丽自己不敢断岁供,只敢去抢新罗的岁供,可百济为着向高句丽表示忠心,竟是三国中第一个停止向大秦纳贡的。
也是在百济背叛之后,新罗再也支撑不住,终于到了使臣殿前哭求救援的这一天。
高句丽暂时没有断绝岁供,那就是还没有要与大秦正面交锋的意思,新罗
毕竟是臣属,大秦不能当真放任新罗被欺压得灭了国,因而派遣使臣玄奖出使高句丽,责令高句丽国主停止进攻新罗。
“回禀陛下,高句丽国主不过傀儡小儿,国中实际是大对卢盖苏文主事。盖苏文此人生性残暴,刚愎自用,不止是新罗,就连高句丽本国国民也对他穷兵黩武怨声载道。”玄奖面带不忿,“微臣带着圣旨前往,是替天子出使高句丽,盖苏文虽然以礼相待,却实则暗含轻鄙,对我朝要求的停战更是嗤之以鼻。还说前朝入侵时,新罗曾经趁乱夺取了高句丽五百里土地,如今攻下新罗城池,不过是收复失地。等完全收复国土之后,自然会停止战争。”
玄奖当即反驳:辽东四郡原本是中国土地,大秦天子尚且没有轻易兴兵夺取,高句丽怎么敢违抗旨意。
盖苏文找不出新的理由反驳,干脆对玄奖置之不理,玄奖只得无功而返。
燕王是性情中人,听了新罗使臣的哭诉已经心怀不忍,听完玄奖一番话,更是怒不可遏,当即上前一步道:“父皇,高句丽自恃地利,屡屡挑衅,先是留存京观炫耀武功,而后修筑长城,分明是心怀不轨,有意防范大秦。今日欺压新罗,待新罗被完全蚕食后,下一个就是趋炎附势的百济。盖苏文野心无可遮掩,当立即压制,以免后患啊!”
朝中不少人纷纷附和,还有人补充道:“高句丽一边交纳岁供,一边修筑长城,在他们眼里,或许这也是在卧薪尝胆,以图后望。”
可也有人提醒:“高句丽地处偏远,地形、气候,都很复杂,易守难攻。前朝东征三次,可都是……”
辽东四郡原是中国故土,前朝皇帝宏图远大,曾倾举国之力三征高句丽,屡败屡战,屡战屡败,打到最后,全国人口损失超过百万,逼得百姓相聚为群盗,各地义军蜂起,更糟糕的是,漠北胡人趁乱度关南下劫掠中原,一时间,饿殍遍野,民不聊生。如今新朝的光景,是轮番胜仗好不容易打下来的,也是几十年休养生息好不容易得来的。
或许盖苏文提起前朝东征,也是对中原天子一次无声的嘲笑。
不提前朝还好,一提起前朝接连失利的旧事,所有武将,几乎所有武将都按捺不住起身要请战。长孙乾达道:“陛下,盖苏文屡屡挑衅,欺压新罗,威逼百济,断绝两国岁供,所图谋的只怕不止两国,剑锋暗指中原。而今四海宾服,万国来朝,无不推崇我中原为天朝上国,新罗、百济是我朝藩属,新罗国主更是忠诚不二,高句丽欺压两国至此,任意施为至此,分明是有意挑衅我大秦。若不出战,各国将如何看待我朝?日后史书刀笔,又该如何评价?”
有燕王与长孙乾达带头,群臣热情越发高涨,声浪几乎就要掀翻太极殿屋顶。皇帝敲了敲凭几,转眼看向缩着脖子,站在角落的小儿子。
“晋王,你说呢?”
晋王支支吾吾:“回禀父皇,儿臣……”
群情激奋之下,他没有出声附和,就说明心里是另有观点,只是碍于情势不肯轻易出口罢了。皇帝耐着性子催了又催,终于催得晋王开口。
“皇兄说的有理,表兄说的也有理。”燕王与晋王一母同胞,都是先皇后所出,这声表兄唤的自然是长孙乾达,晋王细声细语地说,“但前朝败亡殷鉴不远,依儿臣看,还是需要更加慎重才是……”
在众目睽睽之下声音越来越小,几乎含在喉咙里。
这样胆小又示弱,反倒让人不敢再多说些什么,朝上无人反驳,皇帝也不由得又按了按眉心。
“嬴铣。”他叫出徐国公,问道,“你怎么看?”
他是除开晋王之外,另一个从头到尾都没有表达过态度的人。
“众位前辈说得都不错,晋王殿下说得也不错。盖苏文跋扈至此,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百姓陷身水火,正当吊民伐罪。且三国早已归顺我朝,盖苏文既然阴谋叛逆,私建城池,又欺辱新罗君民,大秦发兵平叛,也是师出有名。”
打是一定要打的,确定了要打谁,接下来要商议的则是应该怎么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