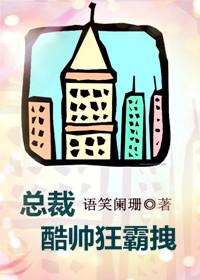笔趣阁>西游:长生仙族从五行山喂猴开始 > 第一百六十三章 性命双全远渡傲来(第5页)
第一百六十三章 性命双全远渡傲来(第5页)
这番道理,说得笃定,讲得透彻。
姜义听着,心里却掀起了波澜。
这几句轻描淡写的话,怕是当年领着自家迈入修行门槛的刘家庄主,也未必能说出个一二三来。
可自家这个儿子,却说得像是自家后院里的一草一木,那般熟悉,那般理所当然。
姜义没再多问。
大儿子的事,他如今是既看不懂,也懒得去懂了。
儿孙自有儿孙福,他只管守好自己这一亩三分地,便足够了。
姜明也未多言,起身回了自个儿的屋子。
屋里,金秀儿正拿着个拨浪鼓,逗弄着自家那个刚会爬的娃儿。
见他进来,也只是抬眼笑了笑,那笑容里,有心疼,也有安心。
到了晌午时分,姜明更是从娘亲柳秀莲手里,半是认真半是玩笑地接过了锅铲。
说是昨夜里大家都辛苦了,今日合该由他这个闲人,来伺候一家老小的五脏庙。
大难过后,一大家子人,总算能齐齐整整地围着一张桌子,吃上一顿安生饭。
席间,气氛还算和睦,唯有姜曦,依旧是板着张俏脸,只是埋头扒着碗里的饭,一言不发。
旁人夹到她碗里的菜,她也不拒,只是偶尔碗筷碰得响了些,泄露出几分心里的不平。
吃过了午饭,姜明也难得没有去后山。
而是随着姜义,去了地里,帮着梳理那些长势正好的药草。
父子二人,一人垄头,一人垄尾,一边慢条斯理地拔着杂草,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
说的,是药草的性味,是真气的流转,偶尔,还会扯到哪本古籍上的某个典故。
金秀儿偶尔会提着水壶过来,给二人送一碗晾好的凉茶。
那模样,倒真有几分寻常乡间,农人耕作的寻常景致。
此后三日,皆是如此。
姜明入了那性命双全的境界后,反倒像是彻底放下了修行上的事。
一心一意,只陪着家人,洗衣做饭,下地劳作,竟比村里最本分的庄稼汉,还要本分几分。
直到三天以后,晚饭桌上。
一家人正吃着饭,姜明将碗里最后一口饭扒拉干净,搁下筷子,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事一般,开口道:
“近期……我打算出一趟远门。”
桌上的气氛,瞬间便是一滞。
连那兀自生着闷气的姜曦,都停下了筷子,抬起了头。
姜义的心思何等敏锐,这几日大儿的反常,他嘴上不说,心里却早察觉了些端倪。
此刻闻言,倒也不如何奇怪,只是将嘴里的饭菜缓缓咽下,这才抬眼看向他,问道:
“打算去何处?做些什么?”
姜明沉吟了片刻,像在权衡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
半晌,才在心头挑拣出几句无关紧要的话,笑道:
“东胜神洲,傲来国,理些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