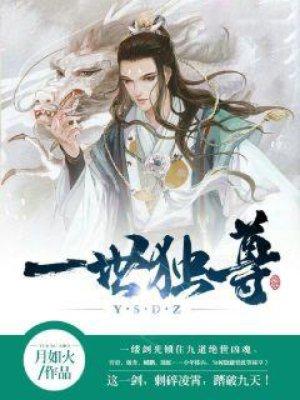笔趣阁>我本将心向沟渠 > 挽留(第3页)
挽留(第3页)
眼看着她没有接茶的意思,顾濯只能将手收回。
“你……来做什么?”他迟疑地问,手指在宽大的袍袖下悄悄蜷紧,试图用那点刺痛来压制心口莫名的悸动。
“来谢你。”祁悠然的目光终于转向他,答得干脆,“我和你们不一样,我不会那些弯弯绕绕的,但我会感恩。欠了的,我认。”
一番话说得坦荡,却也直截了当地伤人。
顾濯怔住,袖中的手指掐得更深了。
“今日来,是为前日育婴堂那场火,”她缓缓道,语气郑重,“我替孩子们来感谢你。”
“举手的事。”顾濯淡淡道。
他避开祁悠然的目光,声音努力维持着那份惯常的淡漠。
空气凝固了,远处蝉鸣愈发聒噪,更衬得室内死寂。
尴尬在屋内发酵。
“难为你,”顾濯突然开口,“待那些孩子……倒很上心。”
话一出口,他便后悔了。
奈何不知道如何补救,只慌忙垂眼,不敢再看她。
“比不得侯爷,”祁悠然嗤笑一声,声音拔高了些,尾音却微微发颤,“当年心硬,如今心善,倒都占全了。”
顾濯沉默下去,只觉得臂上那片伤处,火烧火燎地痛痒起来,直钻进心里去。
“谢礼我让白石交给江烨了。”祁悠然的目光在他那张清冷而苍白的脸上逡巡片刻,从袖中取出一个木匣子,放在两人之间的桌面上,轻轻一推,“这个还给你。”
匣盖打开,露出里面温润的玉色——是那只白玉簪。
顾濯呼吸一滞。
“这簪子……衬你。”他艰难地开口,声音更低,“不必还我。”
祁悠然没应。
“难为你还记得。”她声音带着讥讽,脸上没什么表情,亦是没有做出收回的任何动作。
顾濯微垂着眼,张了张嘴,却是无话可说。
“你先前说的有问题的舆图,差人送来便是。”祁悠然站起身,声音恢复了最初的平淡,“往后,不必再见了。”
话音未落,她转身欲走。
就在裙摆飘起的刹那,一只微凉的手,握住了她的手。
不再是手臂或者是手腕,而是直接探进了她温软的手心。
力道不算很大,却是牢牢地、绝望地。
祁悠然的手指,触到了他未愈的烧伤——凹凸不平、带着新鲜药膏黏腻湿滑的不适触感。
她整个人愣在原地。
顾濯没有抬头。他依旧维持着那个僵硬的坐姿,看不清表情。
只是那只手,固执地、沉默地,没有松开。
空气里,药膏的清苦气与他身上经年不散的、冷冽的雪松气息纠缠,带着些许的狼狈。
窗外的蝉鸣比先前更嘹亮了,尖锐的声浪一波波涌进来,几乎要撞碎这室内的死寂。
那只握着她的手,微微颤抖着,却终究,没有收回去。
“你走之后……”他顿了顿,喉结剧烈地滚动了一下,“我……有些不适应……”声音依旧干涩,“能不能……”后面的话,像是耗尽了全身的力气,带着卑微的乞求,“……能不能重新回到我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