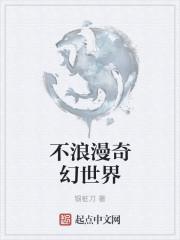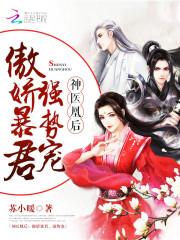笔趣阁>大明第一国舅 > 第672章 大家一起来偷功(第1页)
第672章 大家一起来偷功(第1页)
朱元璋一旦确定要做一些事情,那就十分的果断。
朱?等人才回京的第二天就上朝,朱元璋也直接下旨,封秦王朱?为宗人令,执掌大宗正院。
晋王朱?为左宗正,燕王朱棣为右宗正。
这都是大宗正院。。。
马祖刚踏出韩国公府的门,天边已泛起鱼肚白。晨风拂面,带着几分凉意,他牵着驴儿缓步而行,耳边尚回荡着李善长那句“徐国公,许久未见呐”,语气里有惊、有喜,更有藏不住的试探。他知道,自己这一趟来得突然,却也并非无因。胡惟庸倒台后,朝中风云变幻,李善长虽被削权,但根基未动,门生故吏遍布六部,如今蛰伏府中,看似闲散,实则如冬眠之蛇,只待春雷一响。
可马祖不在乎这些。
他只在乎那一纸脉案??公主无孕,胎息断绝,八月身孕竟成虚妄。这不是寻常滑胎,也不是药石误用,而是有人动了手脚。脉象细弱如游丝,阴血枯竭,阳气不续,分明是被人以极阴之物暗中侵蚀经络,日积月累,终致胎元崩解。这等手段,非精通医理者不能为,更需长期接触饮食起居,方能悄然下药而不露痕迹。
“驴儿,你说,宫里头……有没有鬼?”马祖忽然开口,声音低沉。
驴儿打了个响鼻,四蹄轻快,并不答话。
马祖冷笑一声:“若说没有,我信不过自己的手;若说有,我又不信这世间真有魑魅魍魉。可偏偏,这事就摆在眼前。”
他想起昨夜华利炎诊脉后的沉默,那眼神里的震惊与恐惧,不是装出来的。一个能凭脉知男女的神医,面对这种反常之症,竟也束手无策。而李存义那一声“舅舅安坏?”,亲热中透着小心翼翼,像是在试探他的态度。还有刘姝宁,那个一向敦厚的老臣,说起“大弟过几天就要动身了吧”时,目光闪烁,似有意若无意地避开了他对视。
一切都不对劲。
马祖心中早有疑云,只是未曾点破。临安公主怀胎八月,突然失子,消息封锁极严,连马寻都是偷偷递信才得知。若非他是国舅,又是御前公认的“能断生死”的奇医,此事恐怕连外人都不会知晓。可正因为他是国舅,才更要小心。朱元璋最恨结党营私,尤忌外戚干政。哪怕他救过皇后、稳过龙胎,一旦涉足皇室隐秘,稍有不慎,便是万劫不复。
但他不能不管。
不只是因为亲情,更是因为那孩子??若是男胎,将来便是皇子,血脉关乎国本;若是女胎,也是皇家骨肉,岂容他人暗害?更何况,那方子……是他亲自开的调养汤药,每一味药材都经他亲手验看,煎煮过程也有专人监督。若真出了问题,第一个被问责的,就是他马祖。
“看来,有人想让我背锅。”马祖喃喃道。
他不再耽搁,加快脚步往自家府邸走去。刚进院门,便见马毓蹦跳着迎上来:“爹!你回来啦!姑母说你要教我们背家训呢!”
马祖摸了摸儿子的头,勉强一笑:“背什么家训?”
“就是‘为子者必孝其亲,为妻者必敬其夫’那段!”马毓朗声道,“我都背熟啦!”
马祖心头一震。这段话,昨日李存义也曾念过,一字不差。当时他还以为只是寻常训诫,如今回想起来,却像是一句暗语,或是某种提醒。
“谁教你背的?”他问。
“姑母啊,还有七叔。”马毓眨眨眼,“七叔说,这是做人的根本,咱们马家子孙,人人都得记在心里。”
马祖眉头微皱。李祺佑年纪尚幼,怎会如此郑重其事地传授家训?除非……有人授意。
他正思索间,忽听内堂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马寻匆匆走出,脸色发白:“舅舅,宫里来人了,说是奉皇后娘娘旨意,请您即刻入宫,不得延误。”
马祖神色不变,只淡淡点头:“知道了。”
他转身走进书房,取下墙上悬挂的一柄短剑??非装饰,乃是他年轻时随军征战所佩,剑身斑驳,刃口仍寒光凛冽。他又从柜中取出一只青布小包,里面是一叠泛黄的纸页,皆是他这些年记录的宫廷药案与脉理心得。
“备车。”他说。
马寻低声道:“舅舅,要不要带些护卫?”
“不必。”马祖摇头,“我去的是皇宫,不是战场。带兵刃已是逾矩,再带人,反倒惹人猜忌。”
马寻还想说什么,却被马祖一眼止住。那一眼,平静如水,却又深不见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