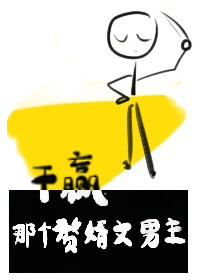笔趣阁>抽象派影帝 > 第414章 还能用我吗(第1页)
第414章 还能用我吗(第1页)
事后。
周乐看着身边像只小猫般蜷缩熟睡的小田,轻轻帮她又盖好了被子。
他拿起手机,屏幕上《ClashofTitans》的数据依旧耀眼,但他心中已开始规划回国后的安排。
接下来几天。。。
雪季再次降临冰岛时,冷芭正坐在“双星园”的木屋窗前修改《抽象派人生》的初稿。窗外风声低回,北极柳的枝干在月光下投出细长的影,像两道并行不悖的轨迹。她手中的钢笔停在纸面,墨迹未干:“我们总以为故事需要高潮迭起,可真正动人的,往往是那些未曾说出口的瞬间。”
周乐从厨房端来一杯热可可,轻轻放在她手边。“又卡住了?”他问,声音里带着笑意。
“不是卡住,是太满了。”她抬头看他,“脑子里全是画面,却不知道该从哪一帧开始剪。”
他坐下,目光落在她摊开的笔记本上。一页页密密麻麻的手写文字间夹着素描、天气记录、甚至一小片压平的苔藓标本。“你还是习惯用手记。”他说。
“机器会遗忘温度。”她轻声道,“而我想记住的,不只是情节,还有那一刻的呼吸、心跳、指尖的凉意。”
他沉默片刻,忽然起身走向墙角的老式投影仪??那是他们拍《极夜长明》时用过的设备,早已淘汰,却被他一直保留着。他插上一根老旧的U盘,按下开关。
银幕亮起,映出一段从未公开的画面:拍摄《极夜长明》第三十七天,暴雪中的临时帐篷内。冷芭蜷缩在睡袋里,额头滚烫,意识模糊。周乐跪坐在她身旁,一手握着她的手贴在自己胸口,另一只手拿着摄像机,低声自语:“她说过,延时摄影能捕捉时间的形状……那我现在录下的每一秒,是不是也能留住她的温度?”
镜头微微晃动,他的声音沙哑:“如果你听得到,别怕。我就在这儿。哪怕全世界都静了,我也会一直说话,直到你醒来。”
画面戛然而止。
冷芭怔住,眼眶瞬间湿润。“这段……你怎么从来没给我看过?”
“那时候你觉得太私密,不适合进纪录片。”他望着她,“我说服李薇删掉了。但原始素材,我一直留着。”
“为什么现在给我看?”
“因为《抽象派人生》不该只是新剧本。”他握住她的手,“它应该是我们所有未完成的对白、所有被风雪掩埋的情绪的延续。你说你想记住温度,那我就把那些时刻还给你。”
她久久无言,最终将头靠在他肩上,像许多年前他们在洛杉矶初次相拥那样安静。
第二天清晨,他们驱车前往雷克雅未克郊外的一座地下熔岩洞穴。这是《抽象派人生》的第一个实勘地点。据当地向导说,这个洞穴形成于八千年前的一次火山喷发,内部结构复杂如迷宫,洞壁布满玄武岩结晶,在灯光下泛着幽蓝微光,宛如星空倒悬。
“像不像我们第一次看到极光那天?”冷芭轻声说。
“更像量子纠缠的可视化模型。”周乐笑,“每一道裂痕都是曾经炽热的路径,如今冷却成永恒。”
他们戴上头灯,一步步深入。洞穴深处有一处天然石台,平整如祭坛。冷芭站上去,环顾四周,忽然说:“就这里了。”
“什么就这里?”
“开场戏。”她转身看他,“女主角独自走进这片地底世界,寻找一种传说中能记录梦境的矿石。她不信神话,但她相信‘如果一个人的记忆足够深,连石头都会记得’。”
周乐凝视她:“这不像虚构。”
“本来也不是。”她平静地说,“这是我母亲去世前最后的愿望。她总说,人走了,记忆就会散。可我不信。我想留下点什么,让未来的人知道她存在过。”
他走近她,没有说话,只是轻轻抱住她。风从洞口灌入,吹动两人衣角,仿佛时间在此刻也放慢了脚步。
当晚回到木屋,冷芭开始重写剧本开头。她不再区分现实与虚构,而是让两者交织生长。女主角的名字叫“林晚”,取自母亲名字中的一个字;男主角则是“陈默”,一名地质录音师,专门采集地球深处的声音波形。
“他录的不是声音,是时间的脉搏。”她在分镜旁注释道,“当林晚问他为什么要听岩石的震颤,他说:‘因为沉默比语言更诚实。’”
周乐在一旁翻阅她早年拍摄的短片资料,忽然发现一张泛黄的照片:2015年云南山区支教期间,冷芭站在一所小学操场上,身后是一群孩子围着一块黑板,上面歪歪扭扭写着“我们要看见星星”。
“你还记得这个?”他指着照片问。
她接过一看,笑了:“当然。那天晚上我们带孩子们做了人生第一次天文观测。有个小女孩问我:‘老师,如果我们看不见星星,它们还在吗?’我当时说:‘只要有人记得,它们就在。’”
“这句话得放进电影里。”周乐认真道,“而且要由孩子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