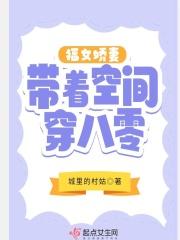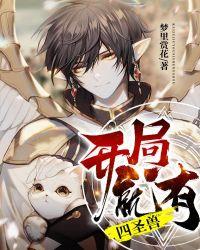笔趣阁>人在大隋刚登基,你说这是西游记 > 第503章 帝辛天喜星之主(第2页)
第503章 帝辛天喜星之主(第2页)
声音凄厉,响彻长街。
差役狠狠抽她一鞭,强行拖走。茶肆内鸦雀无声,众人低头饮茶,仿佛什么都没听见。
玄奘站起身,追出门外,却只见人群散去,唯余地上几点血迹,蜿蜒如蛇。
当夜,他潜入城中最大的忆井旁。那井深不见底,井壁刻满符文,乃是朝廷特设的“净忆井”,专用于定期清洗周边居民的记忆杂质。每逢朔望,便有织忆使前来施法,引井水灌入百姓梦境,冲刷“不当念头”。
玄奘盘膝井沿,取出《还忆录》残卷,开始低声诵读。
他念的是沈砚之的奏疏原文,字字铿锵,句句泣血。念至“民膏尽而官仓盈,忠臣死而佞幸荣”时,井水忽然翻涌,泛起赤红泡沫,竟从中浮出一枚玉简,上面赫然刻着“沈氏一门忠烈”六字!
紧接着,井口四周地面震动,数十道微弱光影自各家屋檐飘出,汇入井中??那是被压抑的思念、被封存的悲愤、被遗忘的真相,在这一刻共鸣苏醒!
玄奘闭目凝神,将全部心力注入诵读。一夜之间,整座乌陵城的百姓做了同一个梦:梦见一位白衣书生立于刑场,临斩前高呼:“史可欺,心不可欺!吾虽死,自有后来者记我名!”
翌日清晨,全城哗然。许多人自发来到忆井边,默默献上纸钱与香烛。有个小女孩把父亲写的族谱偷偷埋在井畔土中,口中喃喃:“爷爷说过,咱们家祖上有个大官,叫沈大人……”
玄奘悄然离去。
他知道,这一夜的诵读,已在人心深处种下怀疑的种子。而怀疑,正是记忆复苏的第一步。
三日后,他抵达巴蜀边界,进入终南山余脉的一片幽谷。此处人迹罕至,唯有几户猎户散居,世代不通外界。然而当他走近村落时,却发现村口立了一块新碑,虽粗糙简陋,却清晰刻着:
>**“此村名守心,住者皆自愿承忆之人。**
>**凡入此村者,请自报三代姓名,否则不得入内。”**
玄奘怔住。
片刻后,一位老猎户走出茅屋,肩扛弓箭,目光锐利:“你是玄奘?”
他点头。
老人忽然跪下,重重磕了个头:“我们等你很久了。”
原来,自从千灯共鸣那一夜后,全国各地陆续出现了类似的“守心村”。它们不在官府户籍之中,由各地自发觉醒的守忆者聚集而成,彼此通过忆井传讯联络,形成一张隐秘的网络。他们不举旗造反,也不聚众抗命,只是坚持一件事??**记住真实的历史,传承真实的姓名**。
在这个村子里,每个新生儿出生,父母都要在他耳边轻诵家族源流;每年清明,全村齐聚,轮流讲述先人事迹;若有外人来访,必须先背出三代直系亲属之名,方可被视为“完整之人”。
玄奘被奉为上宾。当晚,村民围坐在篝火旁,请他讲述记忆回廊中的见闻。他没有隐瞒,一一诉说那些被抹杀者的遗言、那些碑前的对话、那面破碎的镜中幻象。
众人沉默良久,最后一位盲眼老妪开口:“你说大多数人不愿醒来……可你看,我们醒了。哪怕瞎了眼,我也要记住我丈夫是怎么被拉去洗忆堂,回来后连我的脸都认不出的。”
她颤抖的手指向天空:“只要还有一个人记得,真相就不会彻底死去。”
玄奘含泪点头。
数日后,他收到一封密信,由一只青铜飞鸢送来??那是终南山忆源塔独有的传讯方式。信是苏婉儿所写,字迹清瘦却有力:
>**“清忆司已启用‘十重忆刑’,首犯便是你父旧部之后。三人已被捕,将于十五日后公开施行‘魂销术’,令其神识湮灭,永世不得转生。**
>**此外,朝廷派出‘影龙卫’十二人,皆为先天境高手,专司追杀守忆者。为首者名萧烬,乃你幼年同窗,后入清忆司,今已断情绝念,视你为天下第一祸患。**
>**速归,或可救人,或可赴死。”**
玄奘看完,将信投入火中。
火焰升起时,他望着跳跃的光影,想起了很多年前的那个夜晚??父亲被抓走前,把他搂在怀里说:“儿啊,记住,名字是最短的经文,也是最长的祷告。”
三天后,他孤身北返。
途中经过一座废弃驿站,夜宿空屋。半夜,窗外风雨骤起,忽有一道黑影掠入,刀光如雪,直取咽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