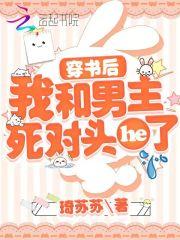笔趣阁>诡目天尊 > 第 480 章 悄 然 蜕 变(第2页)
第 480 章 悄 然 蜕 变(第2页)
林溯站在树顶,望着这张网,低声问:“这是新的共感中枢吗?”
苏芸摇头:“不,这是反共感装置。”
“什么意思?”
“它不让信息涌入,而是阻止情绪泛滥。当一个人试图将自己的痛苦强加于他人时,这条光丝会轻微震颤,提醒施加者:**你正在要求被听见,而非尝试理解。**”
林溯怔住。
他想起自己当年强行维系共感网络的日子,以为只要让更多人彼此听见,就能消除隔阂。可事实是,太多人只是借“共感”之名,行倾倒情绪垃圾之实。他们不想听别人,只想被听见。
这才是真正的失衡。
“所以……我们现在做的,是在教世界‘闭嘴’?”他苦笑。
“不是闭嘴。”苏芸望向远方,“是教会每个人,在开口之前,先问问自己:我说这话,是为了表达,还是为了控制?是为了分享,还是为了索取回应?”
就在此时,终聆之树顶端那只半耳半眼的共生花突然完全睁开。它的瞳孔转向银河系悬臂末端,凝视着“静舟号”即将抵达的目标星球。
花瓣轻颤,落下第一粒花粉。
那不是种子,而是一段加密信息,只有经历过“静默日”并自愿切断共感二十四小时以上的人才能解码。内容极简:
>“欢迎来到寂静之地。
>这里没有回音,所以每一句话都算数。
>若你能忍受三天不说一句话,便可获得一次提问的机会。
>问题不限,答案不定,但必由心出。”
消息传开后,全球掀起一股“沉默潮”。许多人开始尝试每日留出一小时完全禁语,仅靠眼神、手势和书写交流。学校开设“静听课”,学生轮流担任“倾听者”,只能点头或摇头,不得打断。医院心理科引入“空白对话疗法”??医生与患者相对而坐,整整四十分钟不说一字,结束后患者常泪流满面,称“终于感觉被完整地看了”。
三个月后,第一个从“静舟号”传回的数据包抵达地球。
没有图像,没有语音,只有一份文本日志,署名为“第一批静居者?陈默”。
内容如下:
>我们落地了。
>大气可呼吸,水源洁净,土壤含微量蓝晶矿。
>我们拆除了飞船所有远程通讯模块,将其熔铸成一口钟,置于村落中央。
>钟不报时,只在有人完成一次真诚对话后敲响。
>昨夜,小女孩莉亚对老农说:“爷爷,你种的番茄为什么比地球的小?”
>老农没有立即回答,而是带她去看土壤、日照、根系分布,最后说:“因为它不需要长得快,它只需要活得久。”
>莉亚笑了。我们敲了钟。
>这是第一次。
>没有共感,但我们开始懂彼此了。
>原来,距离不是障碍,即时才是。
>当你说完我就答,其实是没给你的声音留空间。
>现在,我们学会等了。
>等风停,等心跳平复,等一句话在心里转三圈再出口。
>我们建了所学校,第一课是:如何独自待着而不焦虑。
>第二课是:如何看着别人的眼睛而不害怕。
>第三课是:当你想说‘我知道’时,请改成‘我听着呢’。
>林溯先生,若您能看到,请告诉苏芸女士??
>她写的‘继续’,我们收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