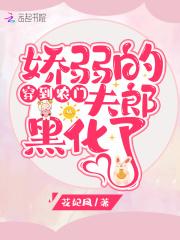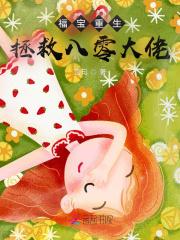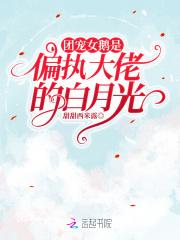笔趣阁>人在东京,抽卡化身大妖魔 > 第371章 十五年前消失的伪人之城新区域的线索达摩试探出师就死(第4页)
第371章 十五年前消失的伪人之城新区域的线索达摩试探出师就死(第4页)
话音落下,她的身体化作无数代码粒子,汇入消散的蓝焰。
“蝉蜕”紧急上浮。
当他们冲破海面时,天空正降下细雪。但奇异的是,雪花落地未融,反而泛起淡淡金光,像是无数微小的名字在低语。
回到陆地一周后,全国范围内出现了罕见现象:
许多家庭报告家中老照片突然显现出新面孔;公园长椅上凭空出现刻有陌生人名字的铜牌;甚至有孩童指着虚空说“奶奶刚刚抱了我”。
专家无法解释,媒体称之为“集体记忆潮汐”。
而葵,在得知一切后,独自前往西山墓园。她在那块无名碑前站了一整夜,天亮时,碑文悄然变化:
>**我曾想拯救世界,却忘了先救自己。
>谢谢你,打断了循环。**
数月后,《归名宪章》迎来第一次修订会议。各国代表齐聚京都,讨论如何应对记忆复苏带来的社会冲击。会上,一位俄罗斯学者提问:“如果不能再依赖系统控制愿力,人类该如何面对无穷尽的悲伤?”
青站起身,播放了一段视频:
东京某小学教室里,孩子们围坐一圈,轮流讲述祖辈的故事。有个男孩说起曾祖父战死前写的家书,说到动情处哭了。旁边女孩递上纸巾,轻声说:“没关系,他听见了。”
画面结束,青说道:“我们不需要控制悲伤。我们需要的,是教会彼此??如何一起哭泣。”
会议最终达成共识:不再建立任何形式的中央管理系统。取而代之的是“社区记忆守护员”制度,由志愿者记录、整理、传承本地历史,形成去中心化的记忆网络。
至于归名之契,某日清晨被人发现静静插在京都御灵堂门前的土地中,刃口朝下,宛如一棵新生的树苗。
上杉澈消失了。
有人说他在北海道开了间小旅馆,专门收留迷失旅人;有人说他去了南美雨林,寻找古代失落的记忆仪式;还有人说,每个下雨的夜晚,都能在墓园听见他低声念诵名字的声音。
但在一本匿名出版的回忆录末尾,有这样一句话:
>**真正的归名,不是让死者归来,
>是让每一个活着的人,
>都有勇气说出那句??
>我还记得你。**
多年以后,一名少女在整理祖母遗物时,发现一本尘封日记。翻开第一页,上面写着:
>“1994年12月21日,晴。
>今天,我把一部分自己送进了大海。
>如果将来有人找到她,请替我拥抱她,
>并告诉他??
>她值得被爱,哪怕她也曾选择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