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为变法,我视死如归 > 第260章 王小仙 我可以罢相(第3页)
第260章 王小仙 我可以罢相(第3页)
她有个儿子,名叫崔承志,曾在禁军任职,十年前莫名失踪,档案被焚。
柳素娥带队赶赴洛阳,在一处废弃道观中找到隐居的老道士。此人原是崔承志贴身侍卫,临终前吐露真相:崔家认定赵昭篡位,因先帝本欲传位于其弟(即崔氏之子),却被权臣矫诏改立太子。母子二人多年来暗中联络旧部,誓要“清君侧、复正统”。此次毁碑之举,正是崔承志所为。
“他恨你不只是变法,”老侍卫咳着血说,“他恨你活了下来,而他的母亲……在狱中被活活饿死。”
赵昭听完报告,沉默良久。
他提笔写信,命人送往西北:“崔承志,我知道你在听。我不追究你毁碑之罪,只要你放下武器,回来谈谈。我们可以清算过去的冤屈,但不能再制造新的悲剧。如果你愿意,我愿以兄弟之礼相待。如果你执意复仇,我也不会逃。但请记住??每一个倒在你刀下的人,都不是为了我而死,而是为了一个更好的天下。”
信送出三日后,边关急报:一名独臂男子牵马立于嘉峪关外,身穿破旧军袍,手持断刀,胸前挂着半块玉佩。
守将请示是否射杀。
赵昭回电:“开门,放他进来。备酒,设座。我要亲自见他。”
风雪交加的那一夜,赵昭独自走入关楼。炉火微明,两人相对而坐,二十年恩怨,尽在无言。
良久,崔承志开口:“你为什么不杀我?”
“因为你母亲的冤,确实是我父辈的错。”赵昭平静道,“但杀你,只会再添一条冤魂。我们要打破的,正是这种血债血偿的循环。”
崔承志泪流满面:“可我毁了石碑……”
“碑可以重刻,人心若毁了,就再也立不起来。”赵昭取出那半块玉佩,轻轻拼合,“你看,它碎了,但还能合上。国家也一样。只要我们愿意修补,就不算太晚。”
崔承志伏地痛哭。
次日,他自愿入狱,接受审判。赵昭特赦其死罪,判十年监禁,允其在狱中教授历史课程。后来,他写下《悔罪书》,公开忏悔,并呼吁所有旧势力成员放下仇恨,投身建设。
这本书被印发百万册,成为全国公民教育读本之一。
夏末,第一所“平民大学”在武汉开学。首批录取一千二百名学生,七成来自农村,三成是女性。开学典礼上,赵昭作为名誉校长致辞:
“今天,站在这里的不再是‘天子’,而是一个曾经躲在梁上听政事的孤儿,一个差点饿死在逃难路上的少年,一个无数次想放弃却咬牙坚持下来的赶路人。
我希望你们记住:知识不属于特权,它属于每一个渴望光明的眼睛。
你们不必感激我,只需记得??当你们走出校门那天,要去照亮更多看不见光的人。”
台下掌声如雷,经久不息。
秋分时节,全国女童入学率达到百分之八十九,首次超过男童。西部干旱地区建成十八座水库,惠及三百余万民众。铁路贯通南北,从北京到广州仅需三天。法庭判决中,首次引用《民法通则》保障农民工工资权益。
而那面镜子,正如承诺所言,已挂在每一所学校、卫生所和派出所的墙上。
孩子们第一次看清自己的脸。
他们笑了。
赵昭站在西北高原的一所小学外,看着一群孩子围在镜前叽叽喳喳,有的整理头发,有的学着鞠躬,还有一个小男孩认真地说:“我以后要当科学家,造会飞的火车!”
老师笑道:“那你得先学会写字。”
赵昭悄然离去,未惊动任何人。
归途中,他收到一封匿名信,只有短短一行字:
“你赢了。因为人民开始照镜子了。”
他仰望天空,万里无云。
风吹过戈壁,带来远方学堂的读书声。
他知道,这场变法,早已不属于他一个人。
它属于每一个敢说真话的人,每一个不肯低头的人,每一个相信明天会更好的人。
文明的火种,终究燃成了燎原之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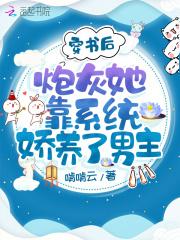
![边疆来了个娇媳妇[年代]](/img/46785.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