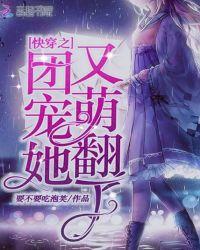笔趣阁>二郎至圣先师 > 334 替罪羊(第1页)
334 替罪羊(第1页)
看着谛听图上的文字,徐永生感到意外。
这趟他本来还考虑在京城多待一段时间,给谛听更多机会。
结果这才刚来没几天便有了成果,徐永生亦为之惊喜。
他再仔细浏览晋升典仪相关内容和细节,通篇。。。
夜深了,终南山的风穿过松林,发出低沉的呜咽。林昭坐在茅屋前的石墩上,手中竹简已被摩挲得发亮,上面是他亲手誊写的《中庸》最后一章:“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月光洒在纸面,字迹如泉涌般清晰,仿佛有无数双眼睛在暗处静静读着。
他放下竹简,抬头望天。北斗七星悬于苍穹,斗柄正缓缓东指??春将至矣。
忽然,远处传来脚步声,不急不缓,踏在积雪之上,没有惊起一片落叶。林昭并未回头,只轻声道:“十年未见,你还是这般轻手轻脚。”
来人一身灰布长衫,背负一把无鞘古剑,面容清癯,眉宇间藏着刀锋般的锐气。正是当年随他走遍七省、后独自入西域求法的弟子沈知白。
“师父。”沈知白跪下,额头触地,“我回来了。”
林昭扶他起身,目光落在他空荡荡的右袖上,心头一颤:“你的手……”
“断于敦煌城外。”沈知白平静道,“那时有一群胡商被官差诬为盗匪,押赴刑场。我拦路鸣冤,反遭围攻。断臂那一瞬,我听见百姓在哭,却无人敢出声。于是我用左手写下‘公道何在’四字,贴于城门。三日后,那批人被赦免。”
林昭闭目良久,终叹一声:“痛吗?”
“比不过人心麻木之痛。”沈知白从怀中取出一卷羊皮,“这是我在龟兹古寺发现的残经,题为《明德真解》,据说是先秦遗书,讲的不是礼法,而是‘心觉’。它说,善非外教,乃本性之光;恶非天生,实为蒙尘之镜。与师父所传之道,竟如出一辙。”
林昭接过,指尖微颤。他翻开一页,见其中有言:“圣人不在庙堂,在田埂,在灶台,在母亲哄孩儿入睡时的一句‘莫说谎’。”他笑了,眼角泛泪:“原来千年前就有人懂得这个道理。”
“可如今,这道理正在被人遗忘。”沈知白声音低沉,“我归途中经河北,见官府强征民夫修陵,孩童失学,老者饿毙路旁。更有士族子弟讥笑义塾学生:‘你们读那些破书,能当饭吃?’有人答:‘不能当饭吃,但能让吃饭的人不忘羞耻。’当晚,那人就被毒死在家门口。”
林昭沉默片刻,起身走进屋内,取出一只木匣。打开后,是一支通体漆黑的毛笔,笔杆刻着细密符文,笔尖似铁非铁,隐隐透出寒光。
“此笔名‘照心’,是我早年游历北疆时,得自一位隐士。他说,执此笔者,可令谎言现形,虚伪崩解。但我从未用过。因为真正的道,不需要神异之力来证明。”
他将笔递予沈知白:“现在,交给你。”
沈知白双手接过,只觉一股暖流顺脉而上,直抵心窍。他猛然睁眼,仿佛看见万千画面奔涌而来:一个少年跪在坟前发誓不再偷窃;一对夫妻和解相拥;一名县令烧毁贪赃账册,自缚请罪……
“这不是幻象。”林昭说,“是天下人心的回响。你看到的,是信念的力量正在苏醒。”
沈知白哽咽:“可我们也失去了太多。李砚去年病逝于岭南,临终前还在抄写《孟子》;陈明远三年前失踪,有人说他进了深山,也有人说他已被秘密处决……我们的人,一个个走了。”
“但他们留下的种子,已在泥土里生根。”林昭望着窗外,“你看那山间的野花,没人播种,没人浇灌,可春风一吹,它们照样开满山坡。人心亦如此。只要火种不灭,终有燎原之日。”
话音未落,远处忽有钟声响起??并非寺庙晨钟,而是铜锣撞击之声,急促而悲怆。
两人对视一眼,同时起身。
不多时,一名满脸血污的年轻人跌进院子,扑倒在地:“师……师父!不好了!山下村庄遭劫!一群蒙面军士闯入,砸了义塾,抢走所有书籍,还将十几个孩子绑走,说要‘斩草除根’!带头之人自称‘奉旨肃清邪说’!”
林昭神色不变,只是轻轻抚了抚案上的《论语》。
沈知白却已拔剑在手:“我去救他们。”
“你去,便是正中其计。”林昭摇头,“他们要的不是孩子,是要逼我现身,是要让天下人以为‘问道者’终究会以暴力回应暴力。一旦动手,十年清誉尽毁,民心也将动摇。”
“那便任他们施暴?”沈知白怒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