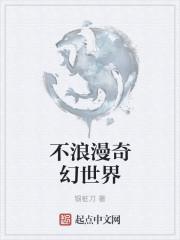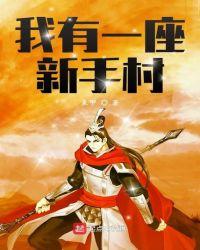笔趣阁>七零易孕娇娇女,馋哭绝嗣京少 > 第666章真是伤风败俗(第1页)
第666章真是伤风败俗(第1页)
方婉如这人心软,想到林晓月刚才那副样子,心里不是滋味。
江舒棠劝了几句,她才想开。
这样的闺女跟江倩倩那样的也没啥区别了,还不如趁早划清界限,不然以后会更麻烦,也算是经验之谈。
晚上顾政南也过来了,两口子带着孩子直接在这边住下了,吃的是香喷喷的卤面条,方婉如做这个很是拿手。
而另一边,方父好久不来,林小鱼咂摸出味儿来了。估摸是自己上次干的那事被发现了,现在方父不敢过来了。
想到方家给的那点钱,以及给。。。。。。
晨光尚未完全铺满小院,灶火已悄然燃起。林溪站在铜锅前,手腕轻抖,蛋液滑入热油的刹那,那声“滋啦”像一把钥匙,打开了记忆深处无数扇门。她没有急于翻炒,而是静静看着蛋清在高温中由透明转为乳白,边缘微微卷起,如同岁月熬煮出的褶皱。
门外传来脚步声,是陈建国提着一篮新鲜鸡蛋进来。“今天来的早。”他把篮子放在案边,目光落在锅里,“还是这道菜?”
“第一课教了多少人,就得从头做多少遍。”她低声道,铲子轻轻压了下蛋饼,“苏晚说,最简单的动作里藏着最深的诚意。”
陈建国没接话,只是蹲下身检查炉膛里的炭火。老宅的灶台用了三代人,砖缝都渗进了油烟香,每一寸都被手掌摩挲得温润。他忽然开口:“昨晚我梦见阿米娜了。她在撒哈拉的一个沙丘上支了口锅,风卷着黄沙打她的围裙,可她还在笑,说‘孩子们今天学会了煎蛋’。”
林溪手一顿,眼眶微热。“她一定还在某个地方做饭吧。也许不是厨房,但只要有人饿着肚子听她说话,那就是她的灶台。”
两人沉默片刻,只听得见锅铲与铜底摩擦的细响,还有屋檐滴水的节奏。一只麻雀跳上窗台,歪头看了她们一眼,又扑棱飞走。
这时,门铃轻响??不是屋顶那口铜铃,而是挂在院门口的新铃铛,是去年孩子们集资换的。来的是皮埃尔的女儿安娜,一个混血少女,穿着洗旧的工装裤,怀里抱着一台老旧录音机。
“林老师,”她声音有些发颤,“这是我爸爸临终前录的最后一段话。他说……如果心音厨房还在继续,就请你当着大家的面放出来。”
林溪接过机器,指尖抚过斑驳的外壳。她认得这台录音机,是当年皮埃尔从巴黎带来的,曾录下无数学员的第一声“谢谢您教会我”。
“好。”她点头,“等中午祭典开始时,我会播。”
安娜鞠了一躬,转身离去。背影单薄却坚定,像极了年轻时的秀兰。
上午十点,第一批返乡者陆续抵达。有从东北赶来的退伍兵,肩上还贴着雪地巡逻时留下的膏药;有刚结束援非任务的医生,行李箱里塞着非洲孩子送的手绘菜单;还有一个坐着轮椅的年轻人,曾因火灾毁容,在心音厨房学会用味觉代替视觉判断火候。
他们不约而同带来了食材:内蒙古的莜面、云南的野生菌、海南的椰浆、甘肃的花椒……堆在院子里,宛如一幅流动的中国地图。
林溪挨个收下,一一记名,然后转身走进厨房。她不再一个人炒菜,而是开始指挥调度:谁切葱,谁烧水,谁负责调味。曾经她是学生,如今成了主厨,可她依旧坚持每道菜尝一口,哪怕只是咸淡。
“你变了。”陈建国一边剁姜一边说。
“我没变。”她擦了擦手,“我只是终于明白,传承不是守住一口锅,而是让每个人都敢点燃自己的火。”
正说着,天空忽暗下来。乌云压顶,风卷落叶,竟似又要下雨。
众人慌忙收拾食材,可就在这时,屋顶铜铃再度响起??不是风吹,而是被人亲手摇动。
所有人抬头望去,只见一个佝偻的身影站在梯子顶端,手里握着铃绳。是那位曾伪造录音的男人,此刻他满脸雨水,衣服湿透,却固执地站着。
“我知道我不配站在这里。”他的声音被风雨撕扯,“但我母亲做的梅干菜,你们尝过了。那是真的。我的心……也想试着回来是真的。”
林溪走上台阶,仰头看他:“你想做什么?”
“我想学。”他哽咽,“从洗锅开始,从零开始。我不想再靠假东西活着了。”
她凝视他良久,忽然转身进屋,拿出一件干净围裙,抛给他:“穿上。先去把后院那三百个土豆削了皮。一个都不能烂。”
男人愣住,随即重重点头,从梯子爬下,直奔后院。
雨越下越大,但没人离开。他们在屋檐下搭起篷布,支起临时灶台,锅碗瓢盆叮当作响。雷声轰鸣中,一道道菜肴接连出锅:酸辣土豆丝冒着泡,红烧肉泛着琥珀光,凉拌黄瓜脆生生地躺在青花瓷盘里。
十二点整,林溪按下录音机开关。
皮埃尔的声音缓缓流淌而出,带着法语特有的温柔尾音:
“亲爱的林溪,当你听到这段录音时,我可能已经回到了大地的怀抱。但请相信,我的心仍在跳跃,因为它记得每一次锅铲碰撞的声音。
我在法国长大,以为美食是艺术,是荣耀,是米其林星星的加冕。直到遇见你,我才明白??真正的烹饪,是跪下来为别人擦去眼泪时,顺手递上的那碗热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