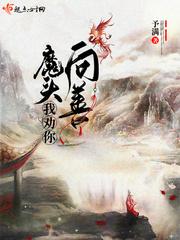笔趣阁>七零易孕娇娇女,馋哭绝嗣京少 > 第675章见到四丫(第1页)
第675章见到四丫(第1页)
小老大笑了,“妈妈,我不怕吃苦,男子汉就是要吃苦,我要向爸爸学习。”
顾政南虽然没当兵,但性格也十分坚毅,孩子们都拿他当标杆。
江舒棠突然就来了兴致,她这个人比较佛系,包括孩子们上学成绩好不好,她都懒得管。
该给的资源给,是那块料,就好好读书,她一定好好供,要不是那块料也没办法,她也不逼着孩子好好学习。
在她看来,能开心幸福的活着,三观正,品德好,这就足够了。
成绩不是衡量孩子的标准,至少在她心里是。。。。。。
石头走后,林溪没有立刻回屋。她坐在院中石凳上,仰头望着满天星斗,耳边是夏夜特有的虫鸣与远处溪流的低语。那本《味觉档案馆》摊在膝上,墨迹未干的字句被晚风轻轻掀动,像在呼吸。她忽然想起重生前的最后一夜??医院走廊惨白的日光灯下,医生摇头说“胎位不正,大人孩子恐怕都保不住”,而她只是死死攥着床单,听见自己微弱的声音:“我不想死……我还想再吃一口热饭。”
那时的她,还不懂什么叫“活着”。
如今她懂了。活着,是吴秀兰闭着眼也能炒出金黄蛋饭的手感;是阿木尔脸上疤痕裂开又愈合后仍敢微笑的勇气;是李长根拄着拐杖用脚趾包粽子时,那一声轻快的“我来”;更是石头趴在地上哭完,还能抬起头说“明天再来”的倔强。
她合上册子,指尖抚过封皮上亲手刻下的八个字:**以味传心,以食渡人**。
第二日清晨,炊烟照常升起。
石头果然来了,手里还攥着那个布娃娃,穿得比昨日干净了些,驼背依旧,但腰板似乎挺了一点。小芸迎上去,递给他一块洗得发白的围裙:“这是你的专属围裙,上面绣了名字。”她指着左胸位置??歪歪扭扭的“石小川”三个字,针脚粗拙却认真。
他低头看着,喉结动了动,没说话,却把娃娃塞进围裙口袋,系带时动作格外小心。
林溪安排他今日学切黄瓜。案板早已换成特制矮桌,刀具也换成了防滑手柄、重心靠前的款式。她站在他身后,双手虚扶在他腕上:“别怕,刀听你的,不是你听刀的。”
石头的手在抖。第一刀下去,黄瓜滚了半截,刀刃卡在木砧里。他脸涨得通红,几乎要退缩。
“再来。”林溪声音很轻,“记住,慢一点,稳一点。你不是在跟菜较劲,是在跟自己对话。”
第三次尝试,他终于切出了第一片完整的黄瓜片。薄厚不均,边缘毛糙,可它是完整的。
“成功了!”小芸拍手。
石头愣了几秒,忽然咧嘴笑了,露出一口参差却洁白的牙。那笑容像破土而出的嫩芽,带着泥土的涩,却无比真实。
中午的菜单是凉拌黄瓜、番茄炒蛋、紫菜蛋花汤。石头主动要求负责凉拌菜。他记得林姨说过:“调味要看人,有人喜酸,有人怕咸,你要学会‘尝’别人的口味。”于是他每调一次汁,就请旁边的小芸尝一口,反复三次,才端上桌。
第一口入口,周振国眯起眼:“嗯,清爽,咸淡适中,还有点回甘??谁做的?”
“我。”石头低声说,头垂着,手指抠着桌角。
“抬头。”周振国用筷子敲了敲碗沿,“做菜的人,有资格看人眼睛说话。”
石头缓缓抬头,对上周振国沉静的目光。那一瞬,仿佛有某种无形的东西,在两人之间完成了交接。
“不错。”周振国点头,“下次加点蒜末,更提味。”
石头用力点头,嘴角又浮起那丝极淡的笑。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石头从洗菜到切菜,从配菜到掌勺,进步缓慢却坚定。他依旧不爱说话,可在厨房里,他的手开始有了节奏,眼神也渐渐敢落在别人脸上。某天傍晚,他竟主动留下帮古丽娜收拾灶台,两人用笨拙的手语交流着油瓶该放哪一格。
林溪看在眼里,记在档中:
>**石头(石小川)**:本周独立完成三道家常菜备料工作,首次尝试颠勺(失败两次,第三次成功翻面)。情绪稳定,社交互动频率提升。昨夜暴雨,他冒雨跑回家取落下的围裙,归来时浑身湿透,却笑着说“不能耽误明天做饭”。
>注:他开始主动整理自己的档案页,用铅笔在“目标”栏写下新一句??“我想做一顿让林姨吃得开心的饭。”
八月中旬,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席卷山村。
连下三日,山路泥泞,河水暴涨。心音厨房的屋顶漏了水,几袋米面被迫转移到高处。最糟的是,通往西南山区的唯一土路彻底中断,原定第二批移动灶支援计划被迫延期。
第四日清晨,雨势稍歇,陈默却匆匆赶来,脸色凝重:“林姐,山里来信了,阿木尔他们被困在老寨村,断粮两天了!最后一只鸡昨晚杀了,今天只能喝野菜汤。通信中断,不知道他们撑不撑得住。”
林溪心头一紧。她立刻召集所有人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