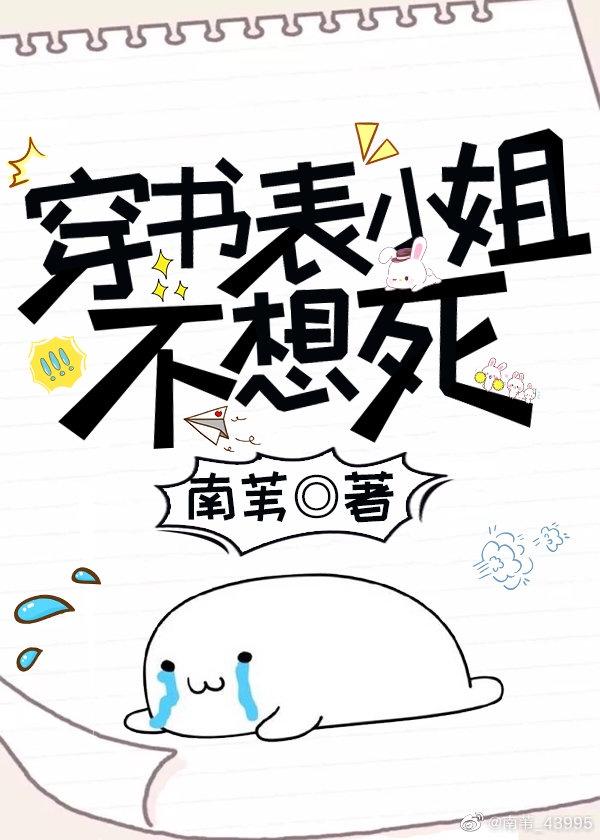笔趣阁>水滸开局在阳穀县当都头 > 第289章 伐宋伐宋(第3页)
第289章 伐宋伐宋(第3页)
此时此刻,苏武正在沙州城下,看到的就是一片土黄,连苏武浑身上下都是土黄之色,城池不大,战爭不难。
只是苏武又一次感觉自己疲惫不堪,近两千里的奔驰,终於到了终点……
军汉们自是爬墙而上,杀得一番人后,城池就开。
站在沙州城墙之上,举目远眺,苏武看的是这片土地的千年往事,也看玉门关在何处。
不知多少年,中原人没见过玉门关长什么样子了……
还不是感怀的时候,调转马头,就是回程,自也留得一部驻防沙州,当要改名,为敦煌。
敦煌就是好听,沙州就是不好听。
回程也是急赶,得快,却是半路之上,就碰到了天子使者,还是程浩。
天子派来追回苏武的人,圣旨自也就在程浩之手。
苏武还问呢:“怎么又是你?”
程浩苦笑:“这般苦差,来去无事,只有急奔,谁人又愿呢?只管是我一拍胸脯,自就到我身上来了。”
也看程浩身上的模样,乾燥寒冷风沙的打磨之下,也不成个人形了。
苏武又笑:“不错不错,这般苦来,你也熬得住。”
程浩笑不出来:“我来的时候,也不知道这一路会这么苦啊,倒也知道是往河西来追你,故人诗词里,说什么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都教他们骗了!”
“不也还说什么大雪满弓刀,羌笛何须怨杨柳吗?”苏武还是笑,自是乐观非常。
程浩哪里有丝毫乐观,只管从背后的布囊里掏出圣旨来,递给苏武,一脸的担忧:“你看看吧……陛下此番真是气怒非常,要换帅了!”
“换帅?”苏武还是笑,接过圣旨,去了火漆,看了看,便是一卷,塞进靴子里,说道:“无妨!”
程浩更急:“你怎么……你心真是大,这还无妨?事关天子信任,事关前程,怎能无妨,你若是教天子不喜,你若是失了宠信,你若是……”
“怎么?怕我连累了你?”苏武插了一语。
程浩当真点头:“岂不是?你若失势,我这好不容易在京城里混出了点脸面,岂不也跟著就没了吗?好不容易才耀武扬威几番,岂不又教人痛打落水狗?”
这大舅子,还真直白。
苏武便笑来:“就凭你能入这河西之地来追我这份苦差,这辈子也当不了落水狗!”
程浩这回,那是真吃得苦头,刚刚从京城去了宥州,再从宥州而回,又立马从京城出发,一直追到了河西之地来。
程浩能这么吃苦,老天……是看得到的。
能吃苦的人,那就有无数的苦可以吃,这辈子可就別想消停了。
程浩却是一语来:“你还能打趣说笑,我都急死了,这一路来,我可睡都不敢多睡,只想赶紧把你追上,你可赶快往那兴庆府去啊,再不去,咱们这一家子,岂不就是落水狗了?”
“这不正去的吗?”苏武安慰一语,却是这事,还没那么快,如今河西已下,就要抽调兵马往河西方向来,如此好让党项人分兵应对。
如此就是三路了,且看党项人那两三万的骑兵,如何去分。
如此,便也是苏武的后勤压力越来越大,还当再从西北各地徵召民夫,给钱,还得给钱!
压力有点大,苏武这一把,几乎是梭哈,他的经济能力,也快到捉襟见肘的地步。
只盼著打破兴庆府与周遭城池的时候,能回一波血来。
党项这么多年的经营,应该家底很是深厚,这个家底,不是粮食之物,而是金银铜铁之物,这东西,在西夏换不到多少物资,但只要苏武把这些东西运到大宋,那就是盆满钵满。
而且,西夏还有一个重大的產业,那就是盐业,这得把持住,一旦西夏变成了大宋,那这盐业就是源源不断的財路。
自是就去,先回韦州,程浩自又往东京回去復命,苏武显然越来越喜欢程浩了,不为其他,这大舅子,没过过几天真正的好日子,还真就是这种家庭出来的男人,能经事能干事,最有奋斗的动力。
先在韦州见种师道,分兵,种师道这边分兵四万进驻武威,以辛兴宗为帅,辛兴宗那是脸都笑开了,浑身上下是干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