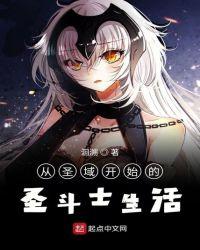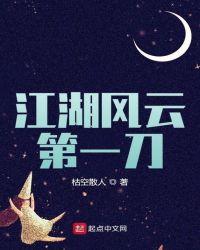笔趣阁>全家夺我军功,重生嫡女屠了满门 > 第676章 被搜家见红流产了(第4页)
第676章 被搜家见红流产了(第4页)
老兵浑身剧震,扑通跪地,泣不成声:“我想找……我想找所有没名字的人……求您,告诉我他们的名字……让他们回家……”
白衣人微微一笑,伸手虚引。
刹那间,塔内灯火通明,无数卷轴自空中垂落,如同星河倾泻。每一卷上,都清晰写着一个名字,一段生平,一句亲人遗言。
“都在这里。”他说,“只要你愿意读,我就永远写。”
老兵含泪接过第一卷,颤巍巍展开,朗声念道:
>“陈阿弟,浙江绍兴人,十七岁参军,战死于嘉定三年秋。临终前托战友捎信回家:‘娘,儿未能尽孝,但记得吃药,天冷加衣。’其母守寡五十年,每日摆一副碗筷于桌旁,呼其乳名‘阿弟’,直至九十高龄含笑而逝。”
话音落,远方某座荒村老宅中,尘封多年的木柜突然开启,柜顶瓷碗自行倒满清水,袅袅升起一缕白气,似有人轻叹:“儿啊……你回来了……”
这一幕,在全国各地重复上演。
有人梦见亡妻坐在床边梳头,笑着说:“今天有人念了我的名字。”
有孤寡老人半夜惊醒,看见窗台多了一双小时候穿的布鞋,旁边放着一张纸条:“爸爸,我是你丢了的女儿,现在我来找你了。”
甚至皇宫深处,那位曾下令推行《禁忆令》的老皇帝,在弥留之际睁开浑浊双眼,望着虚空喃喃:“春妮……春妮……对不起……我以为忘了就能太平……可你们一直在等我……”
他咽下最后一口气时,枕边《轮回图》自动焚毁,灰烬拼成两个字:
>**“晚了。”**
而真正的救赎,才刚刚开始。
十年后,大唐设立“铭恩节”,每年九月初九,全国停乐一日,专用于诵读遗名。孩童入学第一课,便是手持蜡烛,绕校园行走一周,边走边念:“我不忘,我不惧,我有名。”
崔元衡寿终正寝前,留下遗言:“吾一生设阵守塔,原以为防的是外敌。今方知,最该防范的,是我们心中的怯懦与谎言。”
他的墓碑无名,唯刻一行小字:
>**“他曾为名字而战。”**
又二十年,林小满百岁寿辰。
岛上孩童齐聚,欲为她立碑。
她摇头拒绝,只道:“若真要刻什么,就写一句给后来人的话。”
于是,碑林新增一石,正面空白依旧,背面镌刻:
>**“当你看到这块碑时,请记住:有人曾为你不肯遗忘。”**
当日黄昏,海天交接处霞光万丈。
林小满倚门远望,忽见浪尖浮起一枚小小贝壳,随潮水抵达岸边。拾起一看,壳内字迹犹新:
>**“姐姐,下一个世界,轮到我来写了。”**
她笑了,将贝壳放回沙滩。
晚风拂面,带来远方学堂的读书声:
>“石头,阿宝,春妮,我们一起回家去。”
>“不怕黑井不怕鬼,只要有人记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