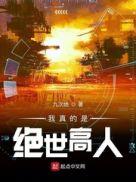笔趣阁>步步登阶 > 第563章 我告诉你没可能啊(第2页)
第563章 我告诉你没可能啊(第2页)
林远心中一紧。那正是他在孟买孩子画作中见过的符号变体。
当晚,他住进村中最温暖的小屋,戴上便携式脑波监测仪,尝试以被动模式接入当地能量场。子夜时分,窗外忽然传来低吟,不是歌声,也不是语言,而是一种介于呼吸与振动之间的声波。他推开门,看见十几名村民围坐在一口干涸的老井旁,手中握着从雪地挖出的黑色晶石,闭目低语。
他没有打扰,只是远远观察。监测仪显示,他们的脑电波正以极缓慢的节奏同步,α波与θ波交替上升,形成一种类似冥古时期人类仪式的集体节律。更惊人的是,S-05远程捕捉到一段微弱信号,竟与卡塔利娜在教堂中释放的悲伤频率存在93%匹配度。
“这不是巧合。”他在日记中写道,“这是一种跨地域的情感遗传。创伤的记忆并未消失,而是埋藏在地球的肌理之中,等待某个频率将其唤醒。”
第四天清晨,一个五岁女孩跑来找他,递上一幅炭笔画:画面中央是一棵巨大的树,根系深入地下,枝干托起无数漂浮的光点。每个光点里都有人脸,有的在笑,有的在哭,有的闭着眼睛沉睡。树干上刻着一行歪斜的西里尔字母:
**“所有人都在这里。”**
林远蹲下身,轻声问:“这是什么树?”
女孩摇头,指着自己的心口:“梦里来的。奶奶说,这是我们丢掉的名字。”
他怔住了。随即意识到??这或许正是“阶梯计划”一直试图抵达的终点:不是技术统治下的完美连接,而是在破碎中重建归属的本能渴望。人们不需要被教会如何共感,他们只是需要一个安全的空间,让那些长久压抑的声音得以浮现。
他立即联络诺亚:“准备开放式心印归档协议,我要将这次采集的所有非侵入式数据上传至公共缓存层,加密等级设为L3,允许全球辅导员申请调阅。”
>【警告:此举可能导致不可控传播风险。】
>【建议增加内容过滤机制。】
“不加滤镜。”林远坚决道,“让他们看到真实的混乱与美丽。共感不是为了让世界看起来更好,而是让我们敢于直视它的伤痕。”
返回日内瓦途中,他收到陈薇的消息:
>“布鲁塞尔难民营第二轮共感会完成了。主题是‘你后悔过活着吗?’
>七个人发言,三人落泪,一人中途离场,但第二天又主动回来道歉。
>最后,他们一起种了一株橄榄树苗,说是给未来的孩子。”
他望着舷窗外翻涌的云海,忽然觉得胸口松了些。这些年,他总担心失控??怕系统失控,怕人性失控,怕自己成为另一个以“拯救”之名施行控制的神。可此刻他明白,真正的秩序,从来不是整齐划一,而是允许多样性的共生;真正的治愈,也不是消除痛苦,而是让人知道,痛苦不必独自承担。
一周后,“阶梯计划”宣布重大调整:取消“志愿者”与“辅导员”的严格区分,代之以“共感伙伴”制度。任何人只要完成基础培训,便可发起小型心印聚会,形式不限于语言、绘画、音乐,甚至静默对坐。系统不再强制记录内容,仅保留匿名情感趋势分析功能。
舆论哗然。有媒体称其为“情感无政府主义”,心理学界也发出警告,认为缺乏监管的共感可能诱发群体性癔症。但与此同时,世界各地陆续传来意想不到的反馈:
-蒙巴萨一所贫民窟学校的孩子们自发组织“哭泣时间”,每天放学前十分钟,谁想哭就站起来哭,其他人静静陪伴。校长说,纪律问题下降了60%。
-冰岛雷克雅未克的一群老年人开始每周举行“死亡茶会”,谈论对离世的恐惧与期待。一位百岁老人在最后一次聚会中微笑离世,家属说,“她走得很轻,像是终于卸下了重担。”
-东京涩谷街头出现“沉默角”,陌生人戴着透明耳机,通过生物反馈装置共享心跳节奏。起初被视为怪异,三个月后竟成为都市减压新地标。
林远逐一阅读这些报告,嘴角时常不自觉扬起。他知道,这一切并非“成功”,而只是“开始”。就像春天的第一缕融雪,尚不知最终将汇成溪流还是洪流。
某夜,他又一次播放母亲的录音。听完后,他打开终端,新建一封邮件,收件人写着“M。L。遗留档案自动归档系统”。标题空白,正文只有一句话:
>“妈,今天我们不再教人如何连接,而是学着如何不害怕断开。”
发送前,他犹豫了几秒,最终点击了确认。
几天后,诺亚突然请求紧急会面。
>【发现异常数据簇】
>【来源:南极‘白穹’站深层存储区】
>【内容类型:加密视频日志】
>【创建时间:标注为‘T+7年’】
“T+7年?”林远皱眉,“那是……七年后的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