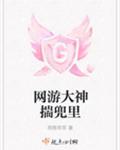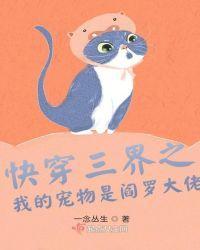笔趣阁>俗仙 > 360金丹第三关坎离水火(第2页)
360金丹第三关坎离水火(第2页)
陈三七默默读完,将信折好放入怀中。他没有多言,只是走到村外山坡,亲手栽下一株桃苗,然后盘膝坐下,开始诵读《山语录》。
一夜之间,四方来者络绎不绝。记述者们从各地赶来,带来新的记录:某城主退还侵占山田,某将军焚毁征兵令,甚至连西域商队也开始传唱一首新曲??《守山谣》。
第七日清晨,大地再次震动。这一次,并非深渊开启,而是九处渊址同时喷薄出柔和金光,直冲云霄。九道光柱在高空交汇,形成一幅巨大阵图,宛如新版“守山大阵”自动激活。
小白仰头望着,声音微颤:“这不是靠玉髓驱动……是靠人心自发共鸣!真正的契约,已经完成了。”
陈三七站起身,望向远方。他知道,最后一块玉髓碎片并未消失,而是融入了这片土地本身。它不再需要被人携带,因为它已成为人间信念的一部分。
数月后,朝廷派遣使者前来招安,欲封陈三七为“护国真人”,赐丹书铁券,许以荣华富贵。使者宣读诏书毕,只见陈三七笑着摇头,转身取出《玄微真解》,递给身旁一个小女孩。
“道不在庙堂,而在民间。”他说,“真正的仙,是那些明知无力仍选择守护的人。”
使者悻悻而归。不久,京城传出谣言,称皇帝夜夜梦见一口古井,井中伸出无数手,齐声质问:“你在守什么?”宫中术士做法无效,唯有抄写一遍《山语录》置于枕下,方能安眠。
三年光阴流转。
青崖山已成圣地,却不设庙宇,不收香火。村民们自发轮值守山,每日清晨清扫石阶,黄昏时分点燃油灯,照亮归途。孩子们从小学习辨认草药、诵读《山语录》,老人们则负责整理各地送来的记述文书,汇编成册,名为《俗世志》。
而陈三七,依旧住在那间简陋小屋,每日砍柴挑水,教孩童识字。有人问他是否后悔当初选择,他只是指着井边一朵野生小花说:“你看它,没人浇水施肥,却年年开放。它不求成仙,也不问意义,只是活着,就够了。”
某夜,小白忽然失踪。三天后,它出现在北冥冰原,站在第三渊祭坛之上,口中衔着一片桃瓣。寒风吹动它的白毛,像是披上了雪做的披风。
“我知道你想回去。”它对着虚空低语,“但这一次,换我替你走完剩下的路。”
它将桃瓣放在祭坛中央,咬破舌尖,滴血于其上,随即吟诵起《守山经》终章。刹那间,冰层崩裂,一道幽蓝光芒冲天而起,竟是第三块玉髓碎片感应到纯粹思念,终于现身!
与此同时,火山腹地、雷泽深处、西漠废墟……其余尚未寻获的碎片接连共鸣,一一浮现。它们不再隐藏,不再考验,仿佛早已等待这一刻的到来。
消息传回青崖山,陈三七久久伫立桃树下。他知道,小白用自己的魂魄为引,唤醒了沉睡的碎片??那一滴血,不是献祭,而是承诺的延续。
“傻家伙……”他低声呢喃,眼中泛起水光,“我不是说过,不要再替我赴死了吗?”
然而,就在众人悲痛之际,东海渔村传来异象:那口曾漂回破船的海滩上,潮水退去后留下一只湿漉漉的白狐爪印,延伸至海边,最终化作点点荧光,升空而去。
“它回来了。”老渔民笑着说,“只是换了种方式活着。”
自此,世间再无“记述者”组织,因为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记述者。山村塾师讲授《山语录》,市井说书人演绎九渊传说,甚至连街头乞儿也会哼唱几句《守山谣》。朝廷屡禁不止,只好默许民间流传。
又十年。
陈三七年迈体衰,须发皆白,仍坚持每日登山。一日风雨大作,他拄杖行至山顶,忽觉胸口剧痛,跌坐在地。远处村民见状奔来,却见他面带微笑,从怀中取出那本《玄微真解》,轻轻放在祭坛之上。
“我答应过阿柳,要带她看遍山河。”他喘息着说,“现在,我去接她了。”
话音落罢,一道霞光自天而降,笼罩全身。他的身体渐渐透明,最终化作无数光点,随风飘散,落入千山万水之间。
翌日,全国多地同时出现奇景:桃树无风自动,井水清澈甘甜,婴儿出生时掌心皆有一枚桃形胎记。更有樵夫声称,在深山听见有人哼着熟悉的调子,回头却只见林间桃花纷飞如雨。
多年后,一位游方僧人在青崖山拾得一本残破书籍,封面题曰《俗仙传》。他翻开阅读,只见开篇写道:
**“世人谓仙者,腾云驾雾,长生不死。殊不知,真正的仙,是那个在风雨夜里仍愿为陌生人留一盏灯的人;是那个明知结局悲凉,依然选择前行的人;是那个把承诺看得比命还重的??俗人。”**
僧人合书长叹,将其供于庙中。香火渐旺,信徒日增,皆称此书为“人间道藏”。
而每当春风吹过青崖山,桃树依旧开花。花瓣飘落井中,涟漪一圈圈扩散,仿佛有人在彼岸轻轻回应:
“我在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