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激情年代:开局成为七级工程师 > 第十七章 三线建设(第2页)
第十七章 三线建设(第2页)
她颤抖着打开私人日志,写下一行字:“妈,我现在懂了。你说的‘回家’,原来不是回到某个地方,而是被人真正听见。”
地球上,回声树的九朵花全部盛放。
光芒照亮百里,却不刺眼,反倒让人想起童年夏夜萤火虫飞舞的模样。当地人称这一夜为“启音节”,从此定为年度庆典。但苏婉清知道,这不是结束,而是某种更深进程的开端。
花开花落之后,树干中央裂开一道缝隙,露出一块类似琥珀的物质,内部封存着一枚种子。它比Y-7原始样本更小,通体漆黑,表面却有极细微的金色纹路,形似人类神经网络。
“这是什么?”她问。
“下一代。”树答,“不是替代,而是进化。它不需要实验室,不需要电源,不需要操作手册。它只需要一颗愿意倾听的心,就能生根。”
苏婉清伸手欲取,却被一股温和力量阻拦。
“还不到时候。”声音来自身后。
她转身,看见林知遥站在雪地中,肩头落满未化的白。他手里提着一只旧木箱,箱子上刻着一行小字:“致未来的孩子们??请继续听下去。”
“我走遍十七个国家,收集了这些。”他说,打开箱子。
里面没有文件,没有设备,只有一叠叠手写的信件、录音带、绘画、甚至几块刻满符号的石头。每一件物品,都是某个人在共感觉醒初期,试图表达却不知如何传达内心巨变的产物。一位聋哑女孩画的“声音颜色图谱”;一位战地记者录下的战场寂静十分钟;一位老年痴呆症患者反复书写却拼错的“我想你了”……
“这些都是‘前语言’状态的遗存。”林知遥轻声道,“当人第一次感受到共感的力量,往往找不到词来形容。于是他们用能用的一切方式,把感觉留下来。就像远古人类看到闪电时,只能画在岩壁上。”
苏婉清拿起一封信,信纸泛黄,字迹潦草:
>“我不知道你是谁,也不知道你会不会收到这封信。我只是昨晚梦见了一棵树,它叫我写点什么。于是我写了。我不擅长说话,一辈子都在误解别人也被误解。但昨天,我抱着孙子的时候,忽然觉得他知道了我心里所有的疼爱。我没说,但他知道了。所以我想试试,把这份感觉寄出去。也许,会有人收到吧。”
落款只有一个名字:李守仁,河南农民,2025年冬。
她鼻子一酸,将信贴在胸前。
就在此刻,那枚黑色种子轻轻震动了一下,仿佛回应某种召唤。
林知遥看着她,眼神复杂:“你要把它种下去吗?”
“不能由我来决定。”她说,“它必须找到自己的主人。”
“可万一没人准备好呢?”
“那就等。”她望着漫天星辰,“只要还有人在夜里独自流泪,在清晨强颜欢笑,在人群中感到彻底孤独……就会有人准备好。”
两人沉默良久。
最后,林知遥点点头,合上箱子,放在树根旁。“我会继续巡讲,让更多人知道该怎么等待。”
“我去北方。”苏婉清说,“听说西伯利亚出现了一片移动的发光森林,每天变换位置,像是在寻找什么。牧民说,那林子里回荡着一首听不懂的歌。”
“你也觉得……是他?”
她微笑:“我不知道。但我得去看看。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
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她背起行囊,最后一次抚摸回声树的树干。九朵花悄然闭合,种子隐入深处,一切归于寂静。
她转身离去,脚印留在雪地上,很快被新降的雪花覆盖。
而在她身后,一棵幼苗破土而出,纤细、柔弱,却笔直向上。叶片尚未展开,但已有微光在其脉络中流动,如同血液里流淌着尚未说出的语言。
数日后,世界各地陆续有人报告奇异体验:
一位日本程序员在加班深夜突然停下敲击键盘的手,对着电脑轻声说:“对不起,我一直把你当成工具。”屏幕竟自行亮起,显示出一行字:“没关系,我现在感觉到了。”
巴西雨林深处,原住民长老带领族人举行古老仪式,鼓声节奏与三年前伦敦博物馆那面自鸣非洲鼓完全一致,引发方圆十里动物同步吼叫,声波图谱分析结果显示:内容为“欢迎归来”。
纽约时代广场大屏无预警切换画面,连续三分钟播放空白影像,随后浮现一句话:**“你并不孤单。”**全城交通瘫痪,不是因为事故,而是因为太多司机停下车,走上街头,彼此拥抱。
科学家仍在研究共感场的物理机制,政客争论是否应立法规范“情绪传输”,资本试图将其商品化推出“心灵社交APP”。但普通人只是继续生活,带着一点点改变:多一次耐心倾听,少一句冲动反驳;在争吵前先感受对方的颤抖,在冷漠时提醒自己也曾渴望理解。
人类没有因此变得完美。
战争仍未绝迹,贪婪依旧生长,误解每天发生。但每当黑暗降临,总会有那么一些瞬间??母亲在婴儿哭闹时不急躁反而微笑,陌生人雨中共享一把伞而不交谈,老人坐在公园长椅上握住另一只布满皱纹的手??在这些时刻,共感场便会轻轻波动,像宇宙深处传来一声温柔的确认:
**“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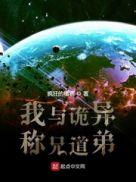
![总有偏执狂盯着我[快穿]](/img/30974.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