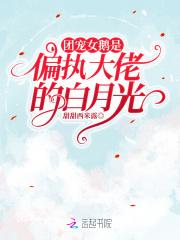笔趣阁>草芥称王 > 第130章 清白之伐为JJM盟主加更(第1页)
第130章 清白之伐为JJM盟主加更(第1页)
吴州罗家的偏房里,地上的青砖吸尽了李青云最后一丝温度。
他蜷缩在地上,身体早已冰凉僵硬。
唯有他那双圆睁的眼睛还没有闭上,瞳孔里凝着几分不甘,像两枚蒙尘的碎琉璃,映着窗外漏进来的微光。
。。。
夜色如墨,浸透了小镇的屋檐与巷道。阿启合上册子,烛火在他眼角投下微微颤动的影子。窗外风起,吹动檐下那口新挂的小铃,叮??一声轻响,像是一句未说完的话终于落下尾音。
他起身吹熄蜡烛,却并未就寝,而是踱步至院中。月光洒在碎陶拼成的碑影上,泛出冷白的光泽。他忽然想起少年时读过的一句话:“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可如今他知道,沉默并非美德,而是压迫的共谋。真正的美,在于敢于开口,在于明知痛仍愿记得。
次日清晨,镇上集市刚刚开张,油条在锅里翻滚,豆浆冒着热气。阿启坐在茶摊边,捧着一碗粗瓷碗装的米汤,看人来人往。一个老妇人蹲在角落卖绣鞋垫,针脚细密,图案是歪歪扭扭的莲花。她身边站着个小女孩,约莫七八岁,正用炭笔在废纸上涂画。
阿启多看了两眼,发现那纸上写的不是字,而是一串名字:王氏阿姑、李三娃、赵婆子……每个名字下面还画了个小圈,像是记账。
“你在写什么?”他轻声问。
小女孩抬头,眼睛亮得惊人:“我在记那些没人说的名字。奶奶说,以前我们家有个姑奶奶,叫阿芸,十五岁就死了,因为写了诗被抓走。我昨晚梦见她,她说她冷,让我给她烧双鞋。”
老妇人抬起头,叹了口气:“这孩子最近总做梦,尽是些古里古怪的事。可我说着说着,才发现……她说的,竟和我娘临终前断断续续讲过的差不多。”
阿启心头一震。
他又一次看见了那种力量??不是来自权力,也不是来自刀剑,而是来自梦、来自耳语、来自某个孩子突然睁开的眼睛。记忆正在以最柔软的方式回归,像春草破土,无声无息,却不可阻挡。
他掏出随身携带的竹笔,在空白册子上写下一行小字:“**梦亦为证。**”
午后,他离开小镇,继续南行。山路崎岖,荒草没膝。途中经过一处废弃驿站,墙垣倾颓,门匾早已腐朽。他本欲绕行,忽见墙根下坐着一人,披着破旧斗篷,怀里抱着一只铜铃,正低声哼唱一首不成调的歌谣。
那声音极轻,却让阿启脚步顿住。
他听出来了??那是《草芥录》第一章的旋律,当年他在西岭村教孩子们的第一课。只是这首歌如今已被改得支离破碎,仿佛传唱者只记得片段,只能凭着感觉填补空白。
“你还记得这首歌?”阿启走近,轻声问。
那人缓缓抬头,露出一张布满风霜的脸,左颊有一道深长的疤,从耳根划至嘴角。但那双眼睛……清澈如泉,映着天光。
是“闻”。
阿启怔住:“你不是刚见过我?”
“那是三天前。”“闻”笑了笑,“我往北去了趟敦煌,回来时听说你路过此地,便在这里等你。”
阿启在他身旁坐下,接过他手中的铜铃。铃身斑驳,内壁刻着细小的文字,凑近才看清是一段祷词:“愿亡者有名,愿生者不盲。”
“这是谁做的?”阿启问。
“一个瞎眼的老铁匠。”“闻”说,“他一辈子替官府修兵器,晚年才知道自己父亲曾是‘静土’实验的首批试药人之一,被活活喂到神志全失,最后死在井底。他花了三年时间,熔了自己的铁砧,铸了这口铃。”
阿启摩挲着铃身,良久不语。
“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吗?”“闻”望着远方山脊,“不是遗忘本身,而是人们习惯了没有名字的生活。他们甚至觉得,祖上无名是一种体面??‘反正都是穷鬼,提它做什么?’可一旦有人开始追问,整个家族的历史就会像塌方一样涌出来,压得人喘不过气。”
“所以你教他们承受?”阿启问。
“不。”“闻”摇头,“我教他们分辨。记住不等于复仇,纪念也不意味着仇恨。我们可以为死者哭泣,但不能让死者的痛苦成为我们拒绝活着的理由。”
一阵风吹过,铃声微荡。
“你说,裴景和如果看到今天这一切,会怎么想?”阿启忽然问。
“闻”沉默片刻,低声道:“他会哭吧。不是为自己脱罪,而是因为他终于明白,他曾以为必须抹去的记忆,恰恰是最该保留的东西。他怕百姓记得太多会造反,却不知道,真正让人站起来的,正是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
“可他也留下了《静土录》。”阿启喃喃,“说明他在最后一刻,选择了留下真相。”
“是啊。”“闻”苦笑,“可惜太迟了。三十年的遗忘,已经让三代人断了根。重建比毁灭难十倍。”
两人并肩坐了很久,直到夕阳西沉,将驿站残墙染成血色。
入夜后,他们在废墟中升起一堆篝火。火光跳跃,映照出彼此苍老的轮廓。“闻”从包袱里取出一本薄册,递给阿启。
“这是我整理的《归名实录》,记录了近三年各地自发举行的‘归名礼’。有些地方,一场仪式找回了七十二个名字;有的村子,连族谱都被烧毁了,只能靠老人口述一点点拼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