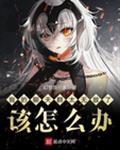笔趣阁>草芥称王 > 第130章 清白之伐为JJM盟主加更(第2页)
第130章 清白之伐为JJM盟主加更(第2页)
阿启翻开一页,只见上面写着:
>**凉州陈家屯,甲辰年清明。
>仪式由八岁女童主持,因其梦见曾祖母托梦诉冤。
>据其描述,曾祖母名唤柳氏,十九岁嫁入陈家,因不肯交出藏粮,被批斗致死,尸体抛入枯井。
>家族原不知此事,经核查旧档案,确有记录。
>当晚,全村燃灯三百盏,置于井口,诵名三遍。
>老人称:‘风里听见了一声谢谢。’**
他又翻了几页,每一条都带着泥土的气息与泪水的温度。
“这些该让更多人看到。”他说。
“已经在做了。”“闻”点头,“已有十几个城镇设立了‘记忆角’,专门陈列这类记录。还有人在编《民间真史汇编》,打算刻版流传。”
阿启忽然笑了:“我们当初只想教孩子认字,现在倒好,竟撬动了一整座历史的大厦。”
“大厦?”“闻”摇头,“不如说是掀开了盖在井口的石板。下面的东西还在往上爬,有些人看见了吓得转身就跑,有些人却跪下来伸手接他们上来。”
第二天清晨,两人分道扬镳。“闻”北上燕州,要去参加一场跨郡的“记忆对话会”,据说会有曾经的加害者后代与受害者家属面对面讲述家族秘史。阿启则继续南下,前往岭南,那里有个渔村世代供奉一口“哑钟”,据传是百年前某位被割舌的渔民所铸,从未响过。
临别时,“闻”递给他一枚小小的铜片,上面刻着一个字:“听”。
“送给你。”他说,“不是命令,是提醒。”
阿启收下,贴身放好。
独自前行的路上,他时常停下歇脚。有时是在古桥边,有时是在荒庙前。每到一处,若有孩童围拢过来,他便掏出碎埙,轻轻一敲,然后问:“你们知道你们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吗?”
大多数孩子摇头。
他就讲故事。
讲一个叫阿芸的女孩如何因写诗而死,讲一个叫李三槐的男人如何饿死在音核基座下,讲西岭村的祠堂如何跪满了寻找祖先的少年,讲回声塔如何从镇魂之器变成了沉默的纪念碑。
孩子们听得入神,有的哭了,有的默默攥紧拳头。
有一次,在一座山村小学外,他讲完故事,一个小男孩怯生生地举手:“先生,我家爷爷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为啥还要翻出来?”
阿启没有立刻回答,而是问他:“你吃过苦菜吗?”
男孩点头。
“苦菜为什么苦?”
“因为它长在土里。”
“不对。”阿启摇头,“是因为它记得雨水太少,阳光太毒,虫子太多。它的苦,是记忆的味道。如果你把它拔出来,洗干净,煮熟了吃,你会发现它其实也养人。可如果你嫌它苦,干脆不让它生长,那土地就会越来越贫瘠。”
男孩若有所思,许久才说:“那……我也想听听我太奶奶的故事。”
阿启笑了。
他知道,这种问答不会永远顺利。在某些城镇,他被人驱赶,斥为“煽动仇恨”;在某些宗祠前,族老怒砸他的竹笔,骂他“败坏门风”。有一次,一群青年围住他,质问他:“你以为你是谁?凭什么决定我们要记住什么?”
他只平静地说:“我没资格决定。我只是把钥匙交给你们??要不要打开那扇门,是你们自己的事。”
后来,那群青年中的一个,三个月后找到他,递上一本手抄簿,说:“我回家问了奶奶,才知道我祖父原来是‘静土计划’的执行医生。他亲手给三百多人注射过药剂,晚年疯了,整天喊‘对不起’。我把这些都写下来了。我不想让他做的事消失,也不想让自己假装清白。”
阿启接过本子,郑重地鞠了一躬。
这一年秋分,阿启抵达岭南渔村。村子依海而建,房屋低矮,晾晒的渔网像灰色的云挂在半空。村中最老的渔民带他来到海边一块礁石前,指着那口锈迹斑斑的“哑钟”。
“一百二十年前,我高祖兄弟叫周阿海,是个识字的渔夫。那年朝廷征粮,村里交不出,他就写了封万民书,结果被抓去割了舌头,关进地牢。临死前,他用血在墙上写下三个字:‘我不忘。’后来家人偷偷把他葬了,又熔了船锚铸了这口钟,说要替他说话。可它……从来没响过。”
阿启伸手抚摸钟身,感受到一种奇异的震动,仿佛内部封存着千年的呐喊。
当晚,他召集全村老少,举行了一场特殊的仪式。他让每个愿意的人写下自己最想告诉世界的遗言或忏悔,卷成纸卷塞进钟腹。然后,他取出碎埙,贴于钟壁,闭目凝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