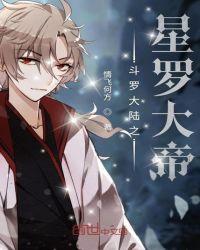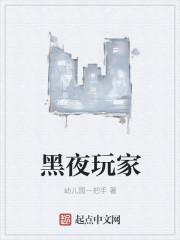笔趣阁>草芥称王 > 第131章 雪里故人(第2页)
第131章 雪里故人(第2页)
“是我老师。”少年眼眶微红,“他教我们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后来他被抓走那天,还在黑板上写了最后一句:‘你们要记得,字是有骨头的。’”
阿启久久无言。
他蹲下身,在树根旁挖了一个小坑,将布条轻轻放入,覆土压实。然后从袖中取出“闻”赠予的铜片,放在土上,低声道:“听。”
风掠过树梢,叶片沙沙作响,仿佛回应。
两人默然良久,直到日影西斜。少年牵狗离去前,回头说:“先生,如果您再去别的地方,请告诉他们,这里有一棵树,替我们记着。”
阿启目送他远去,直至身影消失在林间。
当晚,他在破庙中过夜。夜里又下了小雪,屋内冷得像冰窖。他蜷缩在稻草堆上,却毫无睡意。脑海中反复浮现那棵树、那些名字、那句“字是有骨头的”。他忽然想起少年时代第一次偷读禁书的情景??那时他躲在柴房,借着月光逐字辨认泛黄纸页上的诗句,手指颤抖,心跳如鼓。那一刻,他知道自己再也无法假装无知。
而现在,他不再是那个战栗的少年。他成了别人口中“第一个敢教我们说真话的人”。
可这称号让他不安。
他起身点燃一支残烛,翻开《草芥录?终章》,在末页写下一段话:
>“我从未想成为谁的导师,更不愿被人供奉。我只是拒绝闭嘴,拒绝低头,拒绝让恐惧教会下一代如何遗忘。若有一天人们称我为‘王’,请知那并非权力之冠,而是草芥之命??卑微如尘,却能在石缝中生长,能刺破黑暗,能撑起一方天光。”
写罢,他吹熄蜡烛,躺回草堆。
凌晨时分,他梦见自己变成了一粒种子,被人撒在焦土之上。烈日炙烤,旱风肆虐,四周皆是废墟。但他仍向下扎根,向上伸展。某日,一滴雨水落下,接着又是一滴。然后,整片大地开始震动,无数同类破土而出,汇成一片无边的绿海。海浪翻涌,发出轰鸣,竟是万千人在齐声呼唤同一个名字??不是他的,而是所有曾被抹去者的名讳。
他惊醒过来,窗外天色微明。
起身推门,雪已停,东方泛起鱼肚白。庙前的老槐树静静伫立,枝头积雪簌簌滑落,露出背面写满名字的叶片,在晨光中熠熠生辉,宛如千盏灯笼。
他深吸一口清冽空气,背起行囊,继续南行。
数日后,抵达一座古城。此城曾是“音核工程”的指挥中心之一,如今改造成“真相博物馆”。城门口立着一块巨碑,上书八个大字:“**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两侧悬挂数百铃铛,皆由各地民众送来,每一枚内壁都刻有名册片段。
馆内人流不息。有老人拄拐前来寻找亲人档案,有青年志愿者义务讲解历史真相,还有外国学者专程来访,翻译《民间真史汇编》。阿启混迹人群中,默默观察。
在一楼展厅,他看到一面“忏悔墙”,墙上贴满信件与手稿。其中一封引起他的注意:
>“我是裴景和的孙子。祖父晚年常独自坐在院中流泪,却不肯说为何。直到他临终前,我才从他枕头下找到一本日记。原来他并非完全服从命令,也曾试图销毁部分实验数据,保护几名儿童免受药物测试。但他终究参与了体系,亲手签发过七十三份‘清除令’。
>我无法替他赎罪,只能公开这一切。愿死者安息,愿生者清醒。”
阿启站在信前良久,最终摘下头上旧帽,轻轻放在墙角,作为敬意。
午后,他受邀参加一场青少年读书会。主办方并不知他身份,只当他是普通访客。活动开始后,主持人请每位孩子分享最近读过的最有意义的一本书。
一个女孩站起来说:“我读了《草芥录》影印本。里面讲到西岭村的孩子们跪着找祖先名字,我很感动。我家祖上是官吏,一直说我们家族‘清白显赫’,可我去查老档案,才发现曾祖父曾下令焚烧三十七户人家的族谱,理由是‘肃清异端’。我把这事告诉爸妈,他们很生气,说我‘败坏家风’。但我还是想说出来,因为……我不想活得像个瞎子。”
全场寂静片刻,随后掌声雷动。
轮到阿启发言时,他只说了几句:“你们不必崇拜任何作者,包括写《草芥录》的人。重要的是,你们有没有勇气去问:我家的历史是什么?有没有人因我家族得益而受害?如果答案模糊,那就去找,去查,去听老人讲故事,去翻旧箱子底下的信封。真正的历史不在课本里,而在你们自家的角落。”
散场后,几个孩子围上来,问东问西。有个小男孩怯生生地递给他一幅画:画的是一个老人站在高塔下,手中托着一本书,书页飞出无数小人,每个人手里都举着灯。
“这是我梦见的。”男孩说,“妈妈说您可能就是画里的人。”
阿启接过画,眼眶微热。他摸了摸孩子的头,什么也没说,只将铜片“听”取下,戴在他脖子上。
离开博物馆那日,天空再次飘雪。
他没有立刻启程,而是登上城外一座古塔??正是当年“音核基座”改建而成的“回声塔”。如今塔顶不再播送统一指令,而是接收四方来声。每逢月圆之夜,便会播放收集到的民间录音:有老人讲述饥荒岁月,有母亲哭诉失散子女,也有加害者后代含泪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