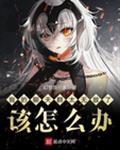笔趣阁>草芥称王 > 第131章 雪里故人(第1页)
第131章 雪里故人(第1页)
杨灿今日穿了一身青缎子箭袖,外罩羔裘,头上戴着熊皮风帽,肩上还披了件羊毛毡斗篷。
他站在树下,雪花落在他的肩头,人如玉树,愈发显得英俊。
阿笑一见,欢喜得一颗心都要跳出来了。
她丢下。。。
雪落了一夜,到清晨才渐渐止息。山间小道被覆盖得洁白无垠,仿佛天地初开,尚未留下足迹。阿启背着竹篓,踏着新雪缓缓下行,脚印一行行延伸向远方的谷口。他不再急于赶路,也不再刻意隐藏行踪。风从林间穿过,带着松针与冻土的气息,拂过耳际时,竟似有低语相随。
他知道,那不是幻觉。
每一步落下,脚下积雪轻响,如同回应某种古老的节拍。他曾以为自己只是个传火者,将零星的记忆点燃于荒原;可如今他明白,火种早已生根,长成了燎原之势。岭南渔村的钟声、燕州对话会上的跪拜、凉州陈家屯的三百盏灯……这些不再是他独行的见证,而是千万人共同书写的续章。
行至半山腰,一座废弃的土地庙出现在视野中。屋顶塌了半边,泥塑神像倒伏在地,脸上爬满青苔。但庙前却整齐摆放着几束干花,还有一只粗陶碗,里面盛着半碗清水,水面映着天光,清澈如镜。
阿启停下脚步。
他在庙檐下歇息,取出随身携带的竹筒,倒出些许炒米,就着雪水嚼食。忽然听见远处传来脚步声,细碎而坚定。不多时,一个少年自林中走出,约莫十四五岁,身穿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肩上扛着一把铁锹,身后跟着一条瘦犬。
少年看见阿启,并未惊慌,反而微微一笑:“您是来看‘名字树’的吧?”
“名字树?”阿启问。
“就是那棵老槐。”少年指向庙后,“三年前,有人在这儿埋了一百个木牌,每个牌子上写一个被遗忘的人名。后来这棵树竟活了过来??它本已枯死多年,连年不下雨,谁也没指望它还能抽芽。可第二年春天,它冒出了绿叶,叶子背面全写着字,像是血沁出来的。”
阿启心头一震,起身随少年绕到庙后。
果然,一棵巨槐矗立在那里,枝干扭曲如挣扎的手臂,树皮皲裂,却生机盎然。最奇异的是,每一片新生的叶子背面,都浮现出墨迹般的文字:**张氏秀英,二十七岁,因藏匿旧书遭拘押,卒于冬寒。****刘大根,十九岁,为护弟妹抢粮被捕,瘐死狱中。****陈阿妹,十三岁,梦中呼母名,被定为‘思想波动’,送入矫正营……**
字迹各异,有的工整,有的歪斜,仿佛由不同人的手一笔笔刻入叶脉。
“这是怎么回事?”阿启低声问。
“没人知道。”少年说,“有人说这是亡魂附树,有人说这是地下骨灰滋养所致。可我觉得……是人心念得太久,土地终于记住了。”
阿启伸手轻抚一片叶子,指尖触到那冰冷的字迹,竟感到一丝温热渗出,如同血脉流动。他闭目凝神,耳边忽然响起无数细语,交织成一片潮水般的低鸣??那是百个名字在同时诉说,是沉默多年的回音终于找到了出口。
他睁开眼,发现少年正静静地看着他。
“你是谁?”阿启问。
“我叫周念。”少年答,“我奶奶是当年‘静土计划’里唯一活下来的记录员。她临终前把一本暗账交给我,说:‘你要替那些没机会说话的人开口。’所以我每年清明都来这儿,给树浇水,读一遍名字,再添一块木牌。”
阿启点点头,从怀中取出《归途纪事》,翻到空白页,提笔写下:“**岭南以北,雪岭之下,有槐重生,叶载亡名。人心不灭,故土遂苏。**”
少年看着他写字,忽然问道:“您是不是……阿启先生?”
阿启笔尖一顿,抬眼看他。
“我在‘记忆角’见过您的画像。”少年声音很轻,“虽然您老了很多,可眼神一样。他们说您走遍天下,只为让人记得不该忘记的事。”
阿启笑了笑,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那你相信记住过去真的有用吗?”他反问。
“有用。”少年毫不犹豫,“去年我们镇上有个老人,一直说自己父亲是烈士,可档案查不到。后来有人提起这棵树,他带全家来了三次,终于在一棵树根旁挖出一枚铜扣,上面刻着他父亲的名字和部队编号。现在,镇政府重新立了碑。”
他说完,从铁锹柄上解下一卷布条,递给阿启:“这是我写的一个人名,能不能也埋进去?”
阿启接过布条,展开一看,上面写着:**林照,三十六岁,教师,因组织学生诵读古诗被判‘文化复辟’,流放西漠,失踪。**
“是你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