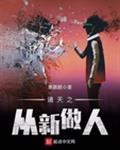笔趣阁>状元郎 > 第三三零章 又要考试了(第1页)
第三三零章 又要考试了(第1页)
对杨斌来说,最有利的选择自然是当回播州宣慰使。不然,他回去只能做‘太上皇’。
杨斌也是学过史书的,知道太上皇可不是什么好职业。日子一久,等儿子彻底大权独揽,他这个老使君真就不如路边一条了……
。。。
夜色如墨,寒风卷着细雪扑打在临安城的青瓦白墙上。朱明远裹紧身上的旧棉袍,踩着结了薄冰的石板路往回走。他刚从国子监值完夜班,手里还攥着一卷未批完的课业文章。脚底打滑,险些跌倒时,他下意识扶住墙边槐树,指尖触到一片湿冷的树皮与积雪混合的泥泞。
“三更天了……”他低声自语,声音被风吹散在巷口。
远处鼓楼传来两声沉闷的更响,已是丑时。这会儿整座城都睡了,唯有御街两侧几盏昏黄灯笼还在风中摇曳。朱明远抬头望了一眼皇宫方向,那里灯火通明??今上素来勤政,据说每日五更即起,批阅奏章至日出不辍。而他自己,一个小小太学助教,却连一顿热饭都难求。
走到自家小院门口,他掏出钥匙开门,却发现门虚掩着。
心头一紧。
屋内油灯尚亮,映出一道人影坐在桌前。那人穿着深青官服,腰佩银鱼袋,头戴幞头,正是礼部员外郎赵景和。朱明远怔住:“赵大人?您怎么……”
“等你。”赵景和缓缓起身,目光落在他冻得发红的手上,“手都裂了。”
朱明远低头看了看,确实,指节处已渗出血丝。他想藏,却被对方一把抓住手腕。
“你可知我为何而来?”赵景和声音低沉。
“莫非是为昨日那份策论?”
“不是策论。”赵景和松开手,从袖中取出一封黄绢诏书,“是陛下亲点,召你入翰林院修撰《资治通鉴续编》。”
朱明远猛地后退一步,撞翻了门边的扫帚。“不可能!我只是个九品末流,从未应过进士科……如何能入翰林?”
“因为你写的那篇《论三代兴衰与本朝得失》,被陛下看了七遍。”赵景和将诏书递上前,“昨夜御前会议,宰执们争论不休,唯独官家一句:‘此人有胆识,敢言人所不敢言,虽布衣亦可用。’”
朱明远呆立原地,脑中嗡嗡作响。
他知道那篇文章是赌命写的。其中直言仁宗朝冗官之弊、神宗变法之激、哲宗复旧之误,甚至暗讽当今皇帝过于宠信宦官典兵。按律,此等文字足以构陷大狱。可没想到,竟得了天子青眼。
“赵大人,这其中必有误会……”
“没有误会。”赵景和打断他,“但你要明白,进了翰林院,便是踏入漩涡中心。有人盼你飞黄腾达,也有人恨不得你死无葬身之地。尤其是……”他顿了顿,“李相那边,不会善罢甘休。”
提到“李相”,朱明远脊背一凉。
李崇安,当朝宰相,三朝元老,门生故吏遍布天下。此人表面宽厚儒雅,实则权欲极重,最忌他人越俎代庖。前年有个小吏因上书言事触及其党羽利益,不出半月便暴毙狱中。如今自己这般被皇帝破格提拔,岂不是公然打脸?
“我可以推辞。”朱明远咬牙道。
赵景和冷笑:“你以为这是恩典?这是试炼。陛下要看看,一个寒门子弟,在无背景、无靠山的情况下,能否守住初心,直面权贵而不屈膝。若你退了,不仅前程尽毁,连累家人也在顷刻之间。”
朱明远沉默良久,终于伸手接过诏书。
指尖触到那烫金纹饰的一瞬,仿佛有股电流窜入心肺。他知道,从这一刻起,自己的命不再属于自己。
翌日清晨,朱明远换上官服入宫谢恩。
新制的绿袍虽不合身,却洗得干干净净。他步行穿过宣德门,经承天门、文德殿,一路行至集贤殿外等候召见。沿途所遇官员无不侧目??一个陌生面孔,既非进士出身,又无显赫家世,竟能步入禁庭?
终于,内侍传唤:“朱明远觐见??”
殿内香烟袅袅,宋理宗端坐龙椅之上,面容清癯,眼神锐利如鹰。
“你就是朱明远?”皇帝开口,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
“草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