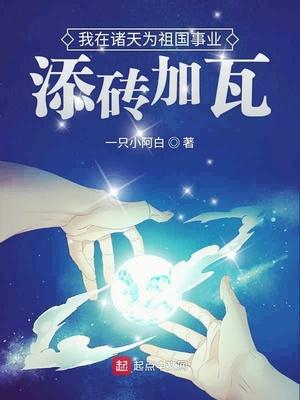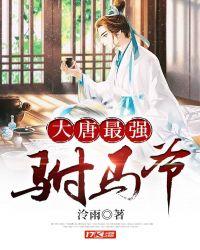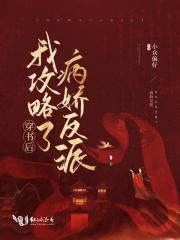笔趣阁>凤谋金台 > 120130(第17页)
120130(第17页)
冯竹晋略皱了眉,手拢袖中,坐在轮椅上,轮椅立在青石砖上,语气淡淡:“哪位主子?”
苏长恩眨了眨眼,轻声压低声音:“还能有哪位?自然是咱们凤仪宫里的那位长公主殿下。”他凑近一步,“快随奴才来吧,殿下亲口吩咐,不见你不安生。”
冯竹晋抬头望了一眼自家宅门,终究没进去。只轻轻叹了口气,挥挥手,小厮又将他推上了另一辆马车,随苏长恩进了宫。
凤仪宫内,檐牙高啄,梅枝微垂。
宫人皆低头行事,殿内一派沉静。
长公主李瑾慧今日身着月白流云襦裙,手执羊脂玉骨扇,坐在雕花梨木罗汉床上,轻轻拨弄着一旁香炉中的香灰,神色平静得仿佛湖水无波。
冯竹晋入殿行礼,她不紧不慢地放下手中扇子,似笑非笑地开口:“冯大人,冯御史,您在朝廷上越发是如鱼得水……架子也大了不少。”
李慧瑾正了正身子,眼里带着打趣,上下打量着他。
冯家现如今是盘散了的棋,冯知节去平定突厥,冯淑娇被朝廷以“安边议和”的名义,册封为“和义公主”,远嫁吐蕃。
如今,冯淑娇身在吐蕃已五年,丈夫吐蕃赞普年迈,政局不稳,且吐蕃新贵对汉人极不友善。她身为汉族和亲公主,处境艰难,只得依靠派驻的使节团与少数亲信自保。
而冯竹晋,作为唯一留在长安的人,除了稳固冯家的地位,更是因为他那副残破的身子,他性情日渐冷峻,喜怒不形于色。
不过他升为监察御史中丞这一路也不干净,三年前,朝中发生“右补阙弹劾刑部尚书挪用赈灾粮款案”。
冯竹晋当时尚是小御史,却提交密折,状告主案官员与刑部尚书暗通款项,在其中揭露了多项账册伪证,手段狠辣、证据扎实。
这是表面,实际上——冯竹晋篡改了部分笔录,将真正主谋的外戚势力置于案外;他又“主动选择了一个替死鬼”——是当时为刑部做外账的账房官,逼其自缢了结;也正因如此,结果得了圣上的意,案子迅速落地,朝中弹冠相庆,他被拔擢为监察御史。
此案在私底下,被称作“割喉换官”。但冯竹晋从不辩解。
旁人问起来,他也只说:“要登得上去,有时就得踩着人往上走。”
这一切,李慧瑾和秦斯礼都看在眼中,不过此时秦斯礼正在岭南与徐圭言厮混,长安的事他尚且不清楚。
“哪里敢在长公主面前摆弄?”冯竹晋笑了笑,“您唤我来是有何事?”
李慧瑾吐出口气,眼眸一紧,像条蛇,盘踞在榻上。
“你倒是淡定。秦斯礼去了岭南,去找你那位夫人——你半点反应都没有?”她语调柔缓,唇角挂着笑,却掩不住那笑容之下的讽意与探查。
冯竹晋负手站立,语气更是平静得像是无波之井:“殿下既然如此关心,那不如问问您自己,您丈夫为何要千里迢迢去往岭南?”
这话一出口,宫中本就稀薄的气息似骤然冷了一寸。
李慧瑾眼神一沉,笑意凝在唇边,半晌才缓缓道:“你倒会挑刺。”
冯竹晋不卑不亢:“我不过是以事论事。若我该有反应,殿下自然也不例外。”
气氛一度凝滞,苏长恩悄悄低头往后退了几步,只盼自己瞬间化为空气。
长公主凝视着他片刻,忽然又笑了:“也好,你这性子,一如既往。但你要知道——你夫人若真的回来了,朝中上下盯着的可不止你。”
冯竹晋听后却只是敛眸,淡淡一拱手:“多谢殿下提醒。”
他转身欲走,长公主却突然问:“那你呢?她若真回来了,你作何打算?你那满屋子的儿子又该怎么和她交代?”
冯竹晋脚步微顿,却没有回头,只留下一句:
“她回不回来,是她的事。至于他们……”他声音压得极低,却透着几分阴鸷的冷意,“那些都是无关的人。”
言罢,轮椅来,声音清脆,慌乱地离去。
李慧瑾坐在殿中,一时怔然,片刻后,轻轻冷笑了一声,扇子敲了敲掌心,唉叹了口气。
,各表一枝。
那夜过后,,床上却尚余余温。
徐圭言静静地靠在床榻一侧,青丝未束,倚着,眼神深沉,指腹摩挲着,神情竟带着一点出奇的温柔。
他们之间忽然多了一种从前未曾有过的和谐。
没有承诺,没有未来,没有那种“你是我的”那般沉重的欲念,更没有承重的誓言,只有当下的温存和喘息。
仿佛这多年来的抗争、别离、挣扎,最终都被时间磨平,只剩下一种妥协的平静。
“世道乱得很,山野之间都是野兽。”秦斯礼轻声说道,手指顺着她锁骨向下滑去,像在描摹旧日未竟的温情,“但现在……我们好像,终于可以喘口气了。”
徐圭言没有应声,只是靠近了一点,半枕着他,闭目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