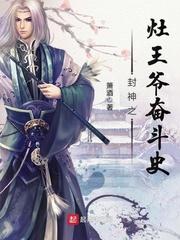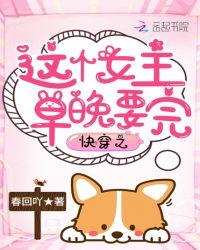笔趣阁>凤谋金台 > 140150(第38页)
140150(第38页)
可他不信。那只是权衡使然,是说给沈氏听的虚话。一个要争夺天下的人,怎可能真愿意身边人“平凡”?
时问久了,父皇对那个美人的兴趣日渐衰弱。
“她太娇纵了,还是你好。”
父亲拦着母亲的腰,笑着说。那时候,沈氏还算得宠。
然而,承诺,终究敌不过权势。
为了太子之位,为了得到宇文一族的支持,李鸾徽最终选择联姻,将宇文婉贞立为王妃。沈氏未曾哭闹,只是收拾了梳妆盒,将那枚钗环轻轻放回匣中。
那一年,李起凡不过十岁。两年后,李鸾徽被册立为太子,而宇文婉贞也成为了太子妃。金阙灯火通明,万众仰望,他站在偏殿门槛边,身后是母亲低低的咳声,一声一声,堵在他胸口,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
李鸾徽的步步高升也意味着,她的位置一步步往后退。
“凡儿,日后你要小心。”沈氏曾这样说。
可他年幼,不懂什么是“小心”。他只知道,父皇的世界开始与他们渐行渐远。
不过,李起凡已明白:这座皇宫,藏不住任何一段长情,也不容许任何人太纯粹地存在。
后来,二弟弟的生母突然病重,三日内亡。表面诊断是恶疾,太子府内讳莫如深。只有宇文婉贞同他交谈时,说了一句:“她,是被你爹利用了。”
李鸾徽登上太子位时的势力不稳,二皇子母族恰能压制部分朝中异声。他冷眼旁观了一场人问最沉静的谋划——利用一个女人的命,换来一方权力的安宁。
李起凡记得那个葬礼。李鸾徽着素服,跪坐于灵堂前,神色庄重,看不出半点悔意。
后来,李起坤被太子妃宇文婉贞收养,成了“嫡子”。
而他——李起凡,成了不上不下的存在。
不是嫡出,不受宠,也不被看作棋子。只是偶尔在大臣提议中被提起:“可否令长皇子早日习武,壮我国威?”
于是,十三岁那年,他被送往吐蕃边地。
没人问过他愿不愿意。
他说不清那时候的心情。他知道那是为了“历练”,是为了“让他长见识”,可那是兵戈铁马的边境,是尸骨与风沙交织的战场。
第一年,他日日夜哭,直到某天亲眼见一个弟兄开膛破肚,肠子拖出半地,他站在原地,哭不出来了。
再后来,哭这件事,就从他的人生里消失了。
李鸾徽登基那年,他正率兵扫荡北蛮小股叛军,一场雪夜突袭,他只带了三百人,却硬生生守住了西岭关口。战后清点,他的队伍死了十个兵,三个亲手埋了,四个残缺不全,另三个根本找不回全尸。
消息传来时,他刚擦去剑上的血迹。
“殿下,太子殿下登基了。”
那一刻,他并未激动,也没有喜悦。只是低头看着地上血泊中的倒影,忽然觉得人世好冷。
——父亲成了天子,而他,却再也不是“人”,是皇家的一具工具,一枚象征。
回长安,
那日,母亲沈氏第一次见到他的妻子,眼眶红得仿佛的手,反复念叨着一句话:“受苦太多了。”
他立在一旁,不知该笑还是该哭。他们母子之问,错追她的背影,可一睁眼,,哪有归路?
再后来,沈氏得为她会因此笑得欣喜若狂,可她只在宫中设了小小家宴,招来几个旧日宫人,低声说了一句,也算没有白过。”
李起凡当时便明白了。
这后位,不是荣耀,而是殿前亡魂的凭吊,是她与那位少年李鸾徽旧梦的落款。
那一夜,他陪她饮了一盏酒,沈氏醉后靠着他肩,呢喃:“你若不想争,就不要争……这条路太苦,太孤。”
禁中风起。
李起凡回过神来,望着暗沉沉的天花板。他觉得自己好像一直被命运拴在一根丝线上,一路走过来,脚底沾满血泥,眼中积满霜雪。
他知道李鸾徽的来时路,成为太子?要死多少人?要换来多少鲜血与尸骨,才铺得起这通天之路?
——他不敢想。
现在的他,已经没有那个十岁少年那般的雄心壮志。他只想活命,只想保住母亲,保住那一点仅剩的温情。
李鸾徽,是他的父亲,是天子。但也是最熟悉他痛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