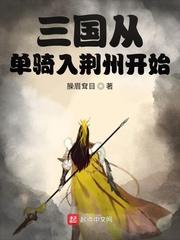笔趣阁>凤谋金台 > 150160(第32页)
150160(第32页)
不能有话说。
李起平坐在下首,规规矩矩地吃饭。
年轻的皇子身着绣金龙纹窄袖朝服,发束整齐,背脊挺直,眉眼间尚带着少年气,却也藏着一丝压抑的疲惫。他没有说话,只默默咀嚼着碗中的饭菜,不时看沈皇后一眼。
今日原本不是他该留在宫中的日子。是沈皇后让人传话,说要见他一面。
他本想只见一面便走,但不知怎的,刚要起身时,却被她一句话留住了:“既来了,就留下吃饭吧。”
她的语气极轻极淡,但却带着无法抗拒的余韵。
李起平坐了下来,自始至终没有再提离开的事。他知道——宫中所有的言语与沉默,都是另一种形式的召唤。
一顿饭吃得颇为压抑,只有碗筷轻响的声音。沈皇后偶尔夹菜,却几乎未动口。王俨则时不时说上几句,“礼部已着手筹备封蕃礼制”,“圣上病体未愈,内务坊人手紧缺”,“今秋气候反常,南边已有水情奏报”……这些话不疼不痒,但又像钝刀子,缓慢地削着人心。
饭后,沈皇后终于放下了筷子,轻声道:“我知道了。你走吧。”
王俨微微颔首,似乎早就等着这句话。他没有多作停留,起身行了一礼,便转身出了寝宫。他的身影在帘幕后消失时,那缕残留的书卷气息也一并散去。
寝殿静了下来,宫人知趣地退去,香烟袅袅,映着沈皇后半倚半坐的身姿,愈发显得形影单薄。
李起平仍坐在原处,没有立刻开口。
沈皇后这才转头看他,声音带着一丝疲惫的沙哑:“我是皇后,你是皇子。等你封蕃,被立为太子之后,要常来宫中。”
她说得缓慢,却无比清晰,像是多年压在胸口的某种嘱托,终于找到了出口。
李起平怔了一下,然后低下头。他的眼睫长而黑,遮住了眼中的复杂情绪。他没有反问,也没有迟疑,只轻声答道:“我母亲常说,皇子都是皇后您的儿子。日后我肯定会常来宫中看您。”
这一句回应说得平稳而体面,恰如其分,没有半分亲昵,却也无不敬之意。
里面含义却深。
沈皇后静静地看着他。她看着这个孩子年少时还常常来向她请安,如今已是即将封蕃的王,言辞谨慎,举止有度,处处恭顺。
可也正因为如此,她才感到一种不可言喻的荒凉。
“你母亲是个明白人。”她轻声说,像是在回忆,又像是在自语,“当年皇子们小的时候,我想着不论嫡庶,能亲厚就亲厚,可人心易变,宫中风急,终究……留不住。”
她顿了顿,又看向李起平的眼睛,语气温柔下来:“你是个好孩子。我知道你不爱说话,也不争事……但若有朝一日,真要你站出来,不许退,也不许让。”
李起平抬头看她,眼中有一瞬间的动容。他张了张口,终究没说什么。
沈皇后望着他,目光渐渐柔软下来。
“你和你哥哥……不一样。”她声音低了,“他太烈,太直。这样的人……在朝堂上,活不长。”
李起平终于问了一句:“他,会死吗?”
沈皇后微微闭眼,像是疲倦到了极点,又像是不愿再看任何人:“我不知道。也不能知道。更不想知道。”
寝殿外传来几声风吹帘响的声音,夜色正悄悄降临。
这一日,是沈皇后最不愿面对的一天。但她却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一切,终究无法逆转。
她缓缓起身,手指微颤,扶着檀木榻边的扶手站起。她步履依旧端庄,但每一步,都沉得像是压着十年心血。
她看了李起平一眼,什么也没说,只摆摆手。
“你回去吧,记得我说的话。”
李起平站起,郑重一礼,退出殿外。他低头行走,步伐沉稳,直到跨出帘幕,方才仰头望了望暗红的天色,轻轻吐出一口气。
宫墙高高,月色未明,风吹得帘幔翻涌,像是掩住了太多将至的哀意。
隔日,晋封大典。
晨光微曦。
沈皇后坐在榻上,披着一件月白色锦缎外袍,面色苍白,神情极淡,像是整个人都被浸在无声的水中。她目光盯着前方,却似没有焦距。
李起平站在她面前,由内侍们为他更衣。今日是他的封蕃大典。
殿中宫人低声小语,替他系上绣金银线的宽带,整好朝冠,抚平垂下的朝袍。他安安静静地站着,不动,也不语。年轻的面庞上是一贯的沉稳,然而他的眼神里,却透出隐约的兴奋与紧张。
沈皇后眼前似有些模糊。她看着这孩子站得笔直,一如多年前李起凡穿上亲王衣冠,满脸意气风发地立在她面前的模样。
只是今日,他的母亲不在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