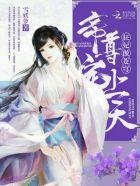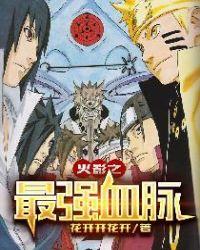笔趣阁>柴刀流漫画大师 > 第137章 奖励(第1页)
第137章 奖励(第1页)
深夜,夏目美绪的房间里依旧亮着灯,她还在等着《链锯人》今天的更新。
虽然已经在坂本健家里看过后面的原稿了,但更新的时候她还是要第一时间追读。
依旧是零点准时更新,她准时点进去,也留下这一话。。。
梨奈的视频在“足迹号”车厢里循环播放了整整一夜。没有声音,只有手语在光影中缓缓流动,像是一阵穿过寂静山谷的风。铃木坐在角落的老式沙发椅上,膝盖上摊着那本边缘卷曲的日记本,笔尖悬在纸面迟迟未落。窗外月光如霜,洒在感应毯尚未收起的接缝处,泛出淡淡银辉。
千夏端着一杯热茶走进来,轻轻放在他旁边的矮桌上。“你看了多少遍?”她问。
“七遍。”铃木低声答,“每一次都像第一次听见。”
千夏坐下,顺手将录音机调到低音量循环模式??那是小满录下的那段话:“谢谢你没有放弃走路。”童声清亮,穿透夜的静谧,仿佛某种无形的锚,把漂泊的心拉回岸边。
“你说,她真的打开了门吗?”千夏望着屏幕定格的画面:梨奈站在舞台中央,双手微微张开,像是拥抱空气,又像是迎接未知。
“不是门。”铃木合上日记本,目光沉静,“是墙。她推倒了一堵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建了多久的墙。”
第二天清晨,阳光刚爬上车顶太阳能板,“足迹号”便启动了新一轮行程。这一次的目的地是一座沿海渔村,那里有一所因台风损毁而临时改建的教学点。孩子们来自散居岛屿的家庭,多数人从未接受过系统心理辅导,更别提什么“情绪共鸣训练”。但他们每天要走三公里山路去乘渡船,脚底磨出血泡是常事,却从没人教过他们如何与疼痛共处。
抵达当天下午,铃木带着设备走进教室。黑板上还残留着粉笔写的潮汐时间表,墙上挂着破旧的渔网和一只褪色的救生圈。五十多个孩子围坐一圈,眼神警惕又好奇。
“今天我们不讲课。”铃木脱下鞋袜,赤脚踩上感应毯,“我们只做一件事??听自己的脚步。”
孩子们愣住。有个男孩小声嘀咕:“走路还要学?我又不是瘸子。”
铃木笑了笑,没反驳。他闭上眼,开始行走。步伐极慢,每一步落下时都伴随着轻微的嗡鸣,投影随即浮现:一道金色轨迹在他身后延展,节奏平稳如呼吸。
“你们知道吗?”他说,“每个人的走路方式,都是独一无二的情绪密码。焦虑的人脚步碎乱,愤怒的人落地沉重,悲伤的人拖着后脚跟……而快乐,并不一定走得快。”
他停下,转向那个说话的男孩:“你叫阿海对吧?来试试看。”
阿海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走上前。当他赤脚踏上感应毯的瞬间,投影骤然变红,节奏凌乱如暴雨击鼓。
全班哗然。
“这……这是我?”阿海瞪大眼睛。
“这是你心里的声音。”铃木轻声道,“你说你不瘸,可你的身体,正在替你说‘我撑不住了’。”
教室陷入沉默。片刻后,一个扎辫子的女孩怯生生举手:“老师……我也想试。”
一个接一个,孩子们轮流走上感应毯。有人步态僵硬得像机器人,有人走得歪斜如同醉酒,还有一个小女孩,几乎不敢抬脚,每迈一步都要停顿数秒。
“她叫小舟。”班主任低声告诉铃木,“去年台风天,她亲眼看着爷爷被浪卷走。从那以后,她再也不敢靠近海边,连走路都怕发出声音。”
铃木蹲在她面前,平视她的眼睛:“你想不想听听大海怎么说?”
小舟摇头,又点头,泪水在眼眶打转。
铃木起身,取出录音机,按下播放键。一段波涛拍岸的录音响起,夹杂着隐约的脚步声??那是他在北极海岸录制的“冰裂行走”,节奏稳定而深远。
“这是海的记忆。”他说,“它记得每一个离开的人,也等着每一个回来的人。你愿意和我一起走一段吗?就当是,替你爷爷回个信。”
小舟咬着嘴唇,终于伸出手,牵住了铃木。
两人并肩踏上感应毯。起初她的脚步颤抖不已,几乎瘫软。但铃木没有催促,只是用自己的节奏包裹她,像潮水温柔地托起浮木。渐渐地,她的左脚抬起、落下;右脚跟进、站稳。一次,两次,十次……
突然,投影变了。原本灰暗的轨迹开始泛出微蓝,节奏竟与录音中的“冰裂行走”逐渐同步。
全班屏息。
当第十八步落下时,小舟忽然抬头,哽咽着说:“老师……我好像……听见爷爷叫我了。”
那一刻,窗外海风穿堂而过,吹动墙上的渔网,发出沙沙声响,宛如回应。
课程结束后,孩子们自发组织了一场“夜行仪式”。他们在沙滩上铺设便携式感应带,赤脚沿着潮线行走,每人录下一小段属于自己的“海之步”。铃木将这些数据整合成一首集体声景作品,命名为《退潮时的脚步》。
当晚,他在日记本上写道:
>有些伤痛不会消失,但它可以学会走路。
>就像浪花终将退回大海,人心也需要一条归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