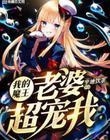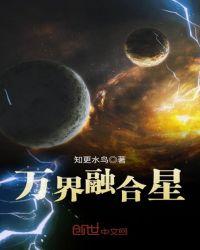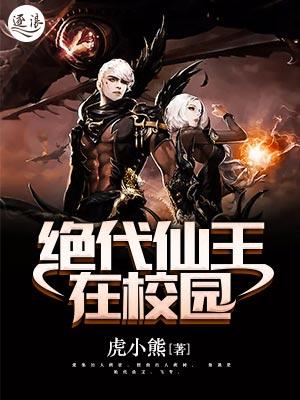笔趣阁>柴刀流漫画大师 > 第137章 奖励(第2页)
第137章 奖励(第2页)
几天后,“足迹号”驶入一座内陆城市,参加一场由教育局主办的教师研修会。主办方原计划让铃木做一场关于“特殊儿童心理干预”的讲座,但他临时更改主题,提出一个大胆请求:请所有参会教师脱鞋,赤脚走过感应毯。
现场一片哗然。
“我们是成年人!”一位资深班主任站起来,“这不是儿戏吗?”
铃木平静地看着她:“那你敢不敢看看,你每天站讲台八小时的身体,在说什么?”
那位女教师脸色微变,最终还是解开了皮鞋扣带。当她踏上感应毯的瞬间,投影赫然显示:双侧重心严重偏移,右腿承压达78%,步频急促且中断频繁。
“你有腰椎间盘突出,对吧?”铃木问。
女人震惊:“你怎么知道?”
“不是我知道,是你身体早就说了上千遍。”他指向数据流,“你一直在忍痛站立,用意志压过信号。可学生呢?他们看得见你皱眉,听得到你叹气,却不知道为什么最近课堂越来越沉闷。”
会场鸦雀无声。
接下来两个小时,铃木带领全体教师练习“支撑步法”??通过调整重心分布、延长摆动周期,减轻关节负担的同时提升存在感。许多人在行走过程中流泪,有人甚至蹲下抱头痛哭。
一位男教师哽咽道:“我已经十年没感觉过‘轻松地站着’是什么滋味了……原来我一直以为的敬业,其实是自我消耗。”
散会前,铃木播放了一段录音??那是某位听障学生写给老师的信,由语音合成器朗读:
【您总说我们要坚强,可您自己走路的样子,让我觉得您比谁都累。我想替您走一会儿,可是我不敢开口。】
全场静默良久。
次日清晨,教育局紧急发布通知:全市中小学将试点推行“教师步态健康监测计划”,并将“足迹号”列为合作单位。文件末尾引用了铃木的一句话:
>教育不是单向灌输,而是双向共振。
>如果老师的心跳都乱了,学生怎么听得见知识?
行程继续推进,冬季悄然来临。“足迹号”北上穿越雪原,前往一所位于边境的孤儿院。这里的孩子大多经历过家庭暴力或遗弃,普遍存在信任障碍。院长说,有个叫拓也的十三岁少年,三年来从未主动与人交谈,甚至连吃饭都躲在角落。
铃木了解情况后,没有急于接触,而是连续三天在院内走廊进行“破冰行走”。每天傍晚六点整,他准时出现,赤脚踩着木地板,以固定节奏往返十次:咚、咚、咚??间隔六秒,力度均匀。
起初,拓也毫无反应。直到第四天,他悄悄出现在楼梯拐角,盯着铃木的脚看了一整晚。
第五天,他坐在走廊尽头的长椅上,等铃木经过。
第六天,他忽然开口:“你为什么总是走这条路?”
铃木停下,转身面对他:“因为这条路通向食堂,也通向宿舍。它是连接‘饿’和‘睡’的桥梁。就像人需要吃饭睡觉,也需要有人知道你回来了。”
拓也低头:“没人等我回来。”
“现在有了。”铃木说,“我每天都在这里走一遍,就是为了告诉你:有人在注意你有没有回家。”
第七天,拓也主动穿上运动鞋,跟在他身后走了全程。
第八天,他脱了鞋,赤脚踏上地板,模仿那个节奏。
第九天,他递给铃木一张纸条,上面画着一幅简笔地图:一条小路从孤儿院延伸出去,绕过雪山,最后回到同一个房子。旁边写着:“我想回去看看,哪怕那里已经没人了。”
铃木收下纸条,点点头:“等春天雪化了,我陪你去。”
那天夜里,千夏在车上整理资料时发现,感应毯记录显示,拓也在模仿行走时,心跳频率首次与外界节奏达成共振??持续达四分三十六秒。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她问铃木。
“意味着他终于允许自己被同步。”铃木望着窗外飘落的初雪,“孤独不是没有陪伴,而是拒绝与世界同频。一旦开始共振,心就有了出口。”
新年临近,“足迹号”返回微光学院休整。坂本健和美绪早已准备好升级系统:新一代感应毯支持生物反馈调节,能根据使用者情绪自动调整引导节奏;车载AI也被训练成可识别百种步态异常,并提供个性化矫正建议。
但铃木否决了全自动方案。
“技术可以辅助,不能替代。”他说,“真正的改变,发生在人与人之间最原始的触碰里??一脚落地,一耳倾听,一眼凝视。”
于是新车载系统保留了手动优先模式,所有核心功能仍需人工介入。唯一新增的是一个小型陶窑??铃木坚持要亲手为每个参与者制作纪念陶人,哪怕耗时费力。
除夕夜,微光学院举办联欢会。“足迹号”停在校门口,车身彩绘映着灯笼红光,宛如一艘即将启航的星舰。小满跑来拉着铃木的手:“老师,我能许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