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从盛夏到深秋 > 云途归心(第1页)
云途归心(第1页)
晨光,是踩着薄雾的脚尖,悄无声息地降临古庙镇的。
远山如黛,近林含烟,那一层夜雨洗礼后的湿意尚未完全褪去,便被初绽的浅金色光线温柔地穿透、包裹。
光线下,能看见空气中悬浮的、极细微的水珠,如同碎钻般闪烁。昨日的紧张、疲惫,乃至那场惊心动魄的救援,都仿佛被这清新的晨光涤荡去了几分惨烈的痕迹,只留下一种劫后余生的、带着轻微钝痛的平静。
松涛居院前,那辆略显陈旧的中巴车引擎已然启动,发出低沉而持续的轰鸣,取代了昨夜此地曾弥漫过的、令人心慌的死寂。
它将载着这支疲惫却坚韧的队伍,离开这片刚刚抚平伤痕的土地,返回那座熟悉的、喧嚣的城市。
团队成员们陆续将行李搬上车厢,彼此间的交谈声也压得很低,似乎不愿打破这山间清晨特有的安宁,也或许是,各自都还带着些昨夜未能完全平复的心绪。
林叙站在车门旁,微微侧着身子,留给众人一个清瘦而沉默的侧影。他左臂规整地悬吊在胸前,雪白的绷带在晨光下有些刺眼。
额前细碎的黑发被带着凉意的山风轻轻吹动,偶尔拂过他低垂的眼睫。
他似乎在专注地看着脚下湿润的泥土,又似乎只是借由这个姿势,来消化和适应昨夜那场情感风暴过后,残留在四肢百骸的、细微的颤栗,以及一种……全新的、陌生到让他几乎不敢确认的平静。
沈知时就在他身侧,大约半步的距离。这个距离,不远不近,既保持了适当的空间,又透着一种无形的关联。
他正与前来送行的当地负责人进行着最后的沟通,声音不高,语速平稳,条理清晰,交代着关于后续地质监测数据传送和应急预案的一些细节。
他看起来与往常并无二致,依旧是那个冷静、可靠的沈工。
然而,若有心观察,便会发现,他那看似专注于交谈的目光,总会时不时地、极其自然地、不着痕迹地扫过身旁的林叙。
那目光停留的时间很短,迅疾如掠过水面的飞鸟,却带着一种沉甸甸的、难以言喻的关切。
“林工,这边上车,小心台阶。”陈工放好行李,走过来,指了指车门处那道不算高、但对此刻手臂不便的林叙来说可能需要留神的台阶,语气是同事间寻常的关照。
林叙闻声抬起头,唇线微动,应了一声低低的“嗯”。他下意识地想抬起未受伤的右手,去扶住那冰凉的车门框,以寻求一个支撑。
然而,就在他指尖即将触碰到金属门框的前一瞬,另一只手臂,一只穿着深灰色棉质衬衫、袖口挽至肘部、露出结实小臂的手,已经先他一步,稳稳地、恰到好处地托在了他右肘的下方。
那只手,骨节分明,修长有力,掌心带着温热的体温,透过薄薄的工装外套布料,清晰地传递过来。
动作流畅而自然,没有丝毫的迟疑或刻意停顿,仿佛只是顺应了某种本能,或者,是早已预设好的程序。
是沈知时。
他甚至没有中断与负责人的交谈,连语速都未曾改变,目光依旧落在对方脸上,侧脸线条在晨光中显得清晰而冷静。
唯有那只托住林叙手肘的手,的存在感,不容忽视。它提供的不仅仅是物理上的支撑力,更是一种沉稳的、无声的安抚。
林叙的身体,在那触碰发生的瞬间,几不可察地僵硬了一下。那是一种长年累月形成的、对于靠近和接触的惯性警惕。
但预想中的、如同受惊鸟儿般的躲闪,并未发生。那僵直只持续了不到半秒,便如同冰凌遇暖,悄然融化。
他微微侧过头,目光极快地从沈知时专注的侧脸上掠过,像是蜻蜓点水,一触即离。然后,他极其轻微地、几乎难以察觉地点了下头。
没有道谢,没有言语。只是借着那只手臂传来的、沉稳的力道,脚步轻捷地一步踏上了车门台阶,身影没入车厢内部的阴影里。
整个过程,短暂,无声。
在外人看来,这或许只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对于伤者的顺手搀扶。但在昨夜那场剖心蚀骨的对话,那个混杂着泪水、颤抖与孤勇的拥抱,以及那句“不要再躲我了”和那个重逾千斤的“好”之后,这个看似平常的动作,其内里蕴含的意义,早已悄然蜕变。
它不再仅仅是“沈工”对合作伙伴“林工”伤势的例行关照,而是“沈知时”对“林叙”,一种更靠近、更亲密、也更理所当然的守护姿态。
是一种试探性的靠近,也是一种被默许的接纳。
林叙在车厢中部选择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将小小的背包放在里侧。车窗玻璃上,映出他有些模糊的面容,以及随后走上车来的、沈知时的身影。
沈知时很快结束了与车外负责人的最后寒暄,迈步上车。
他的目光在车厢内短暂逡巡,掠过几个空位,最终,脚步没有丝毫犹豫地,走向林叙所在的那一排,极其自然地,在他身旁靠过道的位置坐了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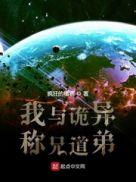
![总有偏执狂盯着我[快穿]](/img/30974.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