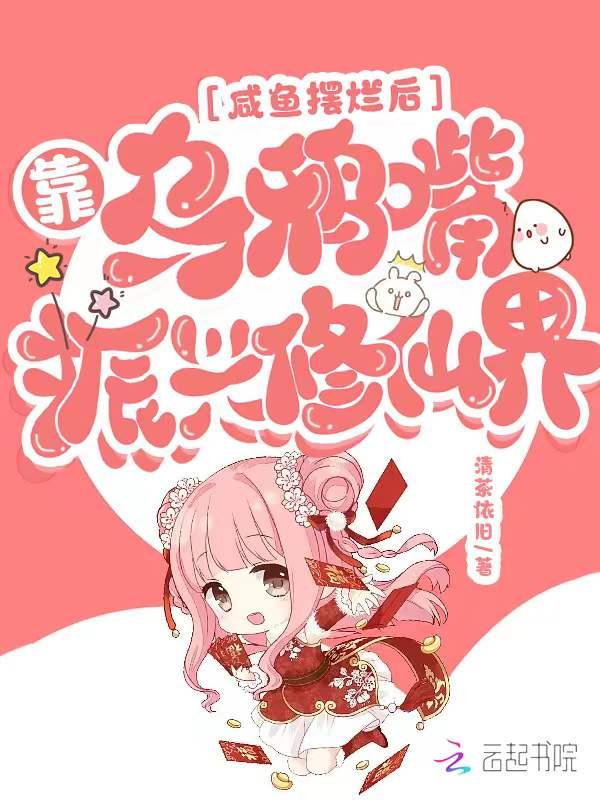笔趣阁>从盛夏到深秋 > 雨拥无声(第2页)
雨拥无声(第2页)
几种激烈到极致的情绪在里面疯狂地冲撞、撕扯,几乎要将他眼底最后一点维持镇定的清明彻底吞噬、湮灭。
“……公家工作最重要,这不是您和爸一直以来教导我的吗?”沈知时的声音终于响起,比平时低沉沙哑了许多,带着一种被逼到悬崖角落、退无可退的克制,以及一种深入骨髓的疲惫。
他试图用对方也曾信奉的“准则”来构建防线,声音里透着一丝几乎难以察觉的、微弱的哀求,“我这么顾全大局,妈,您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他顿了顿,继续解释,语速稍快,像是在陈述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况且不是不去,是我已经提前整整一个月就排定了这次出差行程。会议的级别很高,涉及多方协作,临时推掉,影响会非常大,也……几乎不可能。”
他试图用工作的“重要性”和现实的“不可能”来筑起堤坝,抵挡那汹涌而来的、名为“家庭责任”的潮水。
“不可能?”母亲的声音依旧维持着那令人心悸的平稳,却带着一种洞悉一切、早已看穿所有借口的冰冷嘲讽,“沈知时,你父亲和我,在这个位置上,见过太多‘不可能’最终变成‘可能’的事情。”
周雅茹微微停顿,锐利的目光若有若无地扫过周围那些驻足观望的视线,声音压得更低,却因此更具穿透力,像冰锥一样,精准地刺向目标:“关键在于想不想,在于有没有把该尽的责任、该有的分寸,真正放在心上。”
她的目光重新聚焦在沈知时脸上,带着一种提醒,更是一种无形的施压:“你现在坐的位置,你手上负责的重点项目……里面有多少,是真正凭你所谓的‘一己之力’?别让眼前这一点小小的成绩,就冲昏了头脑,让你忘了根本,忘了是谁当初为你铺的路,搭的桥!”
这话语背后的暗示,如同隐藏在冰面下的暗礁,危险而致命。
沈知时的眼底掠过一丝尖锐的痛楚,他猛地抬高了声音,带着一种被侮辱后的激愤,却又强行压制着:“妈!请你不要乱说!我爸工作严谨,作风清白,从不徇私枉法,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他的声音因激动而微微发颤,“更何况,你们……你们真有那么大的手笔吗?如果真要论依靠,我靠的是我的导师毫无保留的指导,靠的是我的团队成员日夜不休的努力!不是那些……”
“搞学术就应该是干干净净的,就像我爸和你的工作对吗?”
“妈!”他打断了自己可能更激烈的言辞,声音陡然变得沙哑不堪,带着一种近乎崩溃边缘的疲惫和恳求,“你确定我们要在这里,在这个地方,谈这些吗?我们回去谈,好吗?别在这里……别在……”
最后几个字,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带着难以言喻的难堪。
然而,母亲的“体面”从来不代表妥协,反而是更高效的武器。
周雅茹的声音更冷,带着一种精准打击要害的、毫不留情的威胁:“回去谈?当然可以。”
周雅茹向前微微倾身,拉近了与沈知时的距离,声音低到几乎只有他们两人能够听清,却像带着倒钩的冰锥,狠狠扎进沈知时的耳膜,直抵心脏:
“但你最好清楚地认识到一点,”周雅茹一字一顿,确保每个字的分量都足以压垮对方,“你父亲,他很生气。他让我明确转告你,如果你执意如此任性妄为,不把家庭的责任和长辈的用心安排当回事……”
她刻意停顿,欣赏着儿子脸上血色褪尽的瞬间,才继续道:“那么,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支持会彻底停止。
包括他这些年来,不动声色为你经营、铺就的所有人脉、道路……你都可以,不用再考虑了。”
周雅茹直起身,恢复了那副优雅从容的姿态,仿佛刚才那些冰冷的话语并非出自她口。但她的眼神,却比西伯利亚的寒冰更冷、更锐利,带着最终的宣判:
“沈家,不需要一个不识大体、不懂感恩的继承人。”
“江苏那边,有的是比你更懂分寸、更知进退、更清楚自己位置的年轻人,在等着机会。”
“江苏的某位政府高官”——父亲那不言自明的身份和庞大影响力,以及话语中赤裸裸暗示的、收回所有政治资源与人脉支持的威胁,像一记无形的、裹挟着千钧之力的重锤,狠狠地、精准地砸在沈知时最脆弱的心防上。
这远比单纯的金钱断供更具毁灭性。这直接威胁到他事业立足的根基,斩断了他未来向上发展的几乎所有可能性,是要将他这些年的努力和抱负,连根拔起。
沈知时眼底最后一点试图维持的冷静与理智,在这一刻,彻底碎裂,化为齑粉。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冰冷彻骨的怒意,和一种如同坠入万丈深渊的、深沉绝望。那是一种对“体面”之下、赤裸裸的权力操控与情感绑架的、深入骨髓的憎恶与无力。
“妈,”他的声音同样压得很低,却像从万载寒潭深处迸裂出来的冰块,每一个字都带着浸入骨髓的寒意和一种破釜沉舟般的决绝,“我快三十岁了,不是十几岁还需要你们牵着鼻子走的孩子。你们……还有多少年,可以再从头开始,精心培养一个符合你们所有期待的、‘完美’的继承人?”
他顿了顿,目光毫不退缩地迎视着母亲瞬间骤变的脸色,继续道,语气带着一丝嘲讽:“况且,妈你是不是忘记了?我早就经济独立,不靠你们提供的任何钱了。”
他的声音里带着一种孤注一掷的冷硬:“至于那些你们口中‘铺就的路’……随你们的便。我从来没有跪下来求过。我的路,我自己会走。走不通,我认!”
是啊,沈知时快三十了。
他早已不是那个可以被随意摆布、必须仰仗家族鼻息的少年。
这句话,如同平地惊雷,虽然音量依旧控制在最低范围,却蕴含着巨大的叛逆力量,让母亲精心维持的、无懈可击的优雅面具,瞬间出现了清晰的、难以弥合的裂痕。
她的瞳孔骤然收缩,脸上原本得体的淡妆再也掩盖不住骤然褪去的血色。
那双保养得宜、涂着淡色唇膏的嘴唇不受控制地微微颤抖起来,显然被这句在周雅茹听来“大逆不道”、彻底脱离掌控的话语,激起了滔天怒火。那怒火在胸腔里翻涌,却被周雅茹强大的自制力死死摁住,无法在人前彻底失态地爆发出来。
“你……你……”周雅茹你了半天,却没能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挺直如天鹅般的背脊几不可察地晃动了一下,泄露了内心巨大的震动与失控感。
沈知时没有再给她重整旗鼓、继续施压的机会。他几乎是强硬地,带着一种斩断一切退路般的力道,伸出手,扶住了母亲微微颤抖的手臂——那动作看似是子女对长辈的搀扶,实则是一种不容拒绝的、强硬的引导。
他的声音沙哑疲惫到了极点,仿佛所有的精气神都已在刚才那场交锋中被消耗殆尽,只剩下一个空洞的、勉强支撑的躯壳:“走吧,去车上谈。”
话音未落,他已半扶半带着身体僵硬、眼神如同即将喷发的火山般蕴含着骇人怒意的母亲,以一种近乎逃离现场的、却又强装镇定的姿态,快步朝着大楼出口的方向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