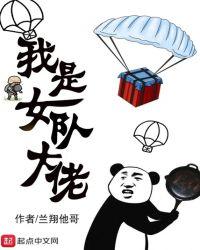笔趣阁>从盛夏到深秋 > 雨夜相拥(第5页)
雨夜相拥(第5页)
林叙在昏暗中,轻轻地点了点头。
这一次,他没有丝毫的犹豫,坦然接受了那份无声的、温暖的邀请,在沈知时特意为他让出的沙发位置边缘,轻轻地坐了下来。柔软的沙发垫因他的重量而微微下陷。
他并没有顺势躺下,而是保持着坐姿,身体微微前倾,手肘支撑在并拢的膝盖上,像一个陷入了深沉思考的哲人。
他垂下眼睛,目光似乎没有具体的焦点,茫然地落在自己那只打着白色石膏、在昏暗中显得格外醒目刺眼的右手上。
过了片刻,在沈知时安静的等待中,他才低声地开口,声音里带着一种近乎自责的困惑,和一种深切的、感同身受般的共情:“我在想……你今天,是不是……真的非常非常难受。”
他顿了顿,似乎在黑暗中努力地组织着更贴切的语言,寻找着能准确表达自己感受的词语,声音轻得像怕惊扰了这夜色,也怕触碰到对方未愈的伤口,“那个拥抱……我当时……只有一只手能用上力气……是不是……根本没抱好?是不是……反而让你……感觉更不舒服了?或者……没能给你足够的……支撑?”
他终于将这个从回來后就一直盘旋在心头、辗转反侧的问题问出了口。
那里面,既包含着对自身因伤而“不完美”的安慰方式的担忧,更充满了对沈知时当时以及此刻感受的、极度的在意与关怀。
沈知时的心,像是被世界上最柔软、最温柔的羽毛,最轻却又最精准地触碰到了内心深处最痛、也最渴望被抚慰的角落。
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林叙在这深更半夜辗转难眠,心里反复思量、感到困扰的,竟然是这个!
他凝视着林叙在昏暗光线中显得格外安静、甚至因此而透出几分易碎感的侧影,看着他无意识地、带着某种歉意般轻轻触碰自己石膏边缘的手指,一股强烈的、混杂着尖锐心疼、巨大感动和难以言喻的温暖洪流,瞬间冲散了他心头盘踞不散的阴霾与身体里沉积的疲惫。
林叙的细腻与温柔,在此刻,以一种他从未想象过的方式,达到了极致,深深地撼动了他。
他没有直接去回答那个关于“抱没抱好”、“舒不舒服”的具体问题。
因为在他心里,那根本不重要,甚至是一个不需要思考的伪命题。他只是默默地伸出手,极其温柔地、却又带着不容置疑的稳定力道,用自己的手,完全地、紧密地包裹住了林叙放在膝盖上的、那只微凉的手。
这个握手,不像办公室里那个激烈颤抖、寻求支撑的紧抓,也不像之前在沙发上倾诉时的虚脱依赖,它带着一种纯粹的、温暖的安抚意味,和一种无比坚定的、传递力量的力量,仿佛在无声地诉说:你做得很好,比这世界上任何一个人所能做的,都要好。
你的存在本身,就是最大的支撑。
“林叙。”他低声唤他的名字,声音在寂静的雨夜里,显得格外清晰,带着一种能够穿透一切迷雾、直抵心灵深处的力量。
“嗯?”林叙应声抬起头,在昏沉的光线中,对上了沈知时的眼睛。
那双他熟悉的眼眸,在此刻的微光下,盛满了太多复杂难辨的情绪——有感动的涟漪,有心疼的波澜,有温暖的洋流,还有一丝如释重负的安宁。
沈知时深深地望进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声音虽轻,却像带着温度的烙印般,清晰而深刻地,直抵林叙的心底:
“谢谢你……今天来找我。”这声感谢,承载了太多无法用言语尽述的意味——谢谢你在研究所走廊里,在我最狼狈不堪、尊严扫地的时刻,停下了脚步。
谢谢你在办公室里,毫不犹豫地推开了那扇门,用你单薄却坚定的身躯,接住了我彻底崩塌的世界;谢谢你此刻的存在,安静地坐在这里,分担我的失眠;谢谢你愿意倾听我那些混乱的、充满负面情绪的剖白;谢谢你……甚至连这样一个细微的、关于拥抱是否足够舒适的细节,都如此放在心上,为之困扰。这简单的“谢谢”二字,其背后所承载的千言万语,重若山海。
林叙彻底怔住了,他张了张嘴,喉结微动,似乎想说些什么。
也许是“不用谢”,这本就是我心甘情愿;也许是“这没什么”,不值得你如此郑重道谢;又或者是其他别的什么。
但所有的言语,在沈知时如此真挚、如此沉重、仿佛倾注了全部心神的感谢面前,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无法承载其万分之一的重量。
然而,沈知时并没有给他组织语言、开口回应机会。
他已经微微倾身向前,将自己的额头,轻轻地、带着全然的信任、深深的依赖、以及一种寻求慰藉与安宁的本能,抵在了林叙未受伤的、温暖的肩膀上。
这个动作发生得无比自然,流畅得仿佛排练过千百遍,仿佛那个肩头的位置,天生就是为他预留的、可以安心停靠的港湾。
没有多余狎昵的动作,没有一丝逾矩的试探,只是这样安静地、全心全意地靠着。
窗外的雨声,不知何时,已渐渐停歇,只剩下偶尔从屋檐滴落的、断续的水滴声,敲打在寂静里。
夜色愈发深沉浓稠,如同化不开的墨。两个曾经在各自人生道路上孤独跋涉、遍体鳞伤的靈魂,此刻在这片温暖的黑暗里静静地依偎着,彼此成为了对方最坚实、最可靠的依靠与锚点。
这一刻,所有的言语都显得多余而嘈杂,唯有心与心之间那无声的、深刻的交流与共鸣,在雨过天晴前最宁静的夜色里,静静地、温暖地流淌着,绵长而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