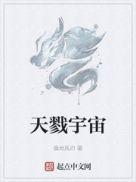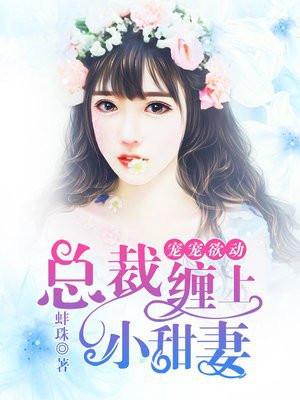笔趣阁>从盛夏到深秋 > 是哦我们什么关系啊(第1页)
是哦我们什么关系啊(第1页)
报告厅内,鼎沸的人声如潮水般缓缓退去,留下满室仿佛仍在微微震颤的空气。
最后一波热烈的掌声余韵似乎还在穹顶下盘旋,最终消散在空调系统低沉的、持续不断的嗡鸣声中。
高处整面墙的落地窗毫无保留地迎入午后偏西的阳光,炽白的光束斜斜地劈入,在深蓝色的厚重地毯上切割出几块巨大的、明亮到刺眼的光斑。
无数微尘在其中不知疲倦地、翩跹起舞,如同被无形丝线牵动的精灵。
沈知时独自站在空旷的讲台前,微微欠身,向台下最后几位尚未离席的听众致意。
聚光灯的光晕尚未完全散去,在他肩头、发梢跳跃,为他周身镀上一层淡淡的、近乎圣洁的光辉。
他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从容得体的笑容,眼中闪烁着项目圆满成功后的欣慰与不容置疑的自豪。
当他的目光状似无意地扫过前排那个固定的位置,准确捕捉到那个熟悉的身影时,那唇角弯起的弧度,便难以抑制地加深了几分,眼底也悄然浸润了一丝难以被外人察觉的、独属于某个人的温暖。
林叙坐在前排靠边的位置,正微微低着头,有条不紊地整理着摊开在膝上和旁边空座上的讲稿、笔记本电脑与参考资料。
他今天穿着一件熨帖得没有一丝褶皱的浅灰色棉质衬衫,袖口被仔细地挽至小臂中段,露出一截线条流畅、肤色白皙的手腕。
数月来困扰他的石膏束缚已在几天前彻底解除,只在腕骨附近留下一圈几乎看不见的、比周围皮肤稍浅淡一点的痕迹,像是时光老人恶作剧般,随手轻轻划过的一道微不足道的注脚。
他的动作从容不迫,甚至带着一种学者特有的、不疾不徐的韵律感。
脸上的神情平静得像一泓深潭,仿佛刚才满场针对他们二人的、毫不吝啬的赞誉与掌声,都与他无关,只是掠过耳畔的一阵微风。
然而,只有当他的视线,在不经意间,如同被磁石吸引般,悄悄掠过台上那个仿佛汇聚了所有光芒的人时,那平静无波的眼底深处,才会极快地掠过一丝难以言喻的、混合着骄傲与认同的暖意——那是共同经历过奋战、攻克过难关后,沉淀下来的、无需言说的默契,与深植于心的欣赏。
沈知时步履从容地走下讲台,几乎是立刻,就被几位热情未减的同仁围拢起来。
一位来自国家古建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急切地探身询问评价体系中关于木构建筑关键榫卯节点安全性的量化指标具体算法。
另一边,两位来自知名遥感数据公司的工程师,则对报告中惊鸿一瞥提到的多源异构数据融合算法的底层逻辑,表现出极其浓厚的兴趣,问题一个接一个。
沈知时游刃有余地在这几个小小的、专业性极强的圈子间切换应对,谈吐清晰,引证得当,既保持了专业的深度,又不失令人如沐春风的亲和力。
他时而用修长的手指在空中轻轻点划,强调着某个关键概念;时而微微倾身,侧耳聆听对方的疑问,眼神专注。
每一个动作都显得自然而优雅,仿佛这种场合对他而言,早已是驾轻就熟。
林叙安静地将所有物品分门别类地收进两人的公文包里,拉好拉链。
然后,他拿起沈知时那个深蓝色的保温杯和一瓶未开封的矿泉水,默默走到人群外围稍远处,倚靠在一张铺着白色桌布的茶水桌旁等候。
他的目光偶尔会不受控制地飘向那个被人群簇拥着的、光芒四射的身影,却又总是在即将被对方察觉的前一瞬,迅速而克制地收回,仿佛只是不经意地扫视过报告厅的环境,或是望向窗外明净的天空。
很快,一位身材微胖、面色红润的地方文物局科长,带着朴实的热情,大步流星地走向林叙。
这位科长声音洪亮,带着北方人特有的爽直,手里紧紧攥着记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脸上写满了求知若渴的真诚。
“林博士!请留步!可算等着您有空了!”科长的语气带着点儿激动,几乎是小跑着过来,“您刚才报告里最后提到的,利用高光谱遥感技术精准识别彩绘层下隐蔽裂隙的那部分,真是太实用了!简直就是为我们市里那座清代戏台量身定做的思路!那戏台的彩画,没得说,顶呱呱,是宝贝!可内部木结构一直怀疑有隐患,我们不敢轻易动,怕修坏了成罪人。您看,依我们这具体情况,从头到尾,该怎么一步步操作最稳妥?”
林叙停下原本准备走向门口的脚步,转过身,神情立刻变得专注而温和。他自然地接过对方双手递过来的、有些卷边的资料和放大的彩色照片,凑近些,在明亮的光线下仔细查看着戏台梁架的细节。
阳光从侧面高大的窗户照进来,在他低垂的、浓密的睫毛下投下一小片细密的扇形阴影。
他用清晰平稳、不带多余感情色彩的语调,结合戏台具体的抬梁式结构、可能的木材病害类型(虫蛀、腐朽、受力疲劳),以及当地的气候环境特征,条分缕析地详细解答着对方的疑问。
他的手指轻轻点在照片上梁柱结合的关键部位,指尖干净,指甲修剪得短而整齐:“在实际数据采集时,如果条件允许,最好能优先选择900纳米到1700纳米这个近红外光谱范围,这个波段对木材内部的密度变化、含水率差异以及早期腐朽最为敏感,穿透力也相对较强。”
他的指尖修长,刚刚摆脱石膏的束缚,动作间似乎还带着一点点重新适应自由后的、不易察觉的生疏和谨慎。
科长听得频频点头,眼中满是敬佩与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