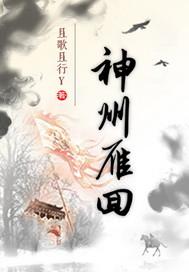笔趣阁>祥子修仙记 > 第220章 漫天枫叶起群狼汹涌出(第1页)
第220章 漫天枫叶起群狼汹涌出(第1页)
按万宇轩的说法,一重天不会有修士,或者说。。。经过二重天肉体改造后的修士,极难适应一重天世界中的凡俗之力。
莫说这些后天修炼的“伪修”,哪怕是那些天生灵根、天赋卓绝的天纵之才,一旦踏上修行之路,。。。
雪停了,天光渐明。乌兰察布的鸣心坛上覆着一层薄雪,像被谁轻轻盖上的棉被。院长仍坐在原地,白发与胡须结了一层霜,呼吸在冷空气中凝成细雾。他没有起身,也没有再问话。他知道,有些存在不需要回应,就像心跳不必向耳朵解释为何跳动。
咔、咔、咔。
那声音从坛底传来,不急不缓,仿佛穿越了千山万水才抵达此处。它不再是孤寂的回响,而像是一条脉络,悄然连接起地球上所有尚未熄灭的心跳。院长闭目,任思绪随风飘散??他想起十年前第一次听见这脚步声时的惊惧,想起林月手记中那句“他不是来救世的,他是来陪人的”,想起那个雪夜,自己跪在坛前,哭得像个迷路的孩子。
如今,他不再流泪。
但他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祥子修的,从来不是长生不死的仙道,而是人心深处那一丝不肯断绝的温热。
忽然,坛面震动了一下。
不是脚步,也不是渗水,而是一种沉稳的搏动,如同大地的心跳。院长睁眼,只见坛心凹槽中的蓝灰石子正微微发亮,绿意如藤蔓般沿着裂纹蔓延,竟在雪中催生出一株嫩芽??三片叶子,纤细却挺立,叶尖挂着露珠,映出整片天空。
他怔住了。
这是第一次,石子孕育出生机。
“你种下的东西……终于要开花了?”他喃喃。
风没回答,但远处传来一阵铃声。清脆、遥远,像是从童年巷口飘来的糖担子铃铛。紧接着,一道影子掠过雪地??不是实体,也不是幻象,而是一道由无数微光拼凑而成的轮廓:旧棉袄、布袋、左耳后的疤痕,在晨光中一闪即逝。
院长笑了,笑得像个终于读懂谜题的孩子。
与此同时,南美洲安第斯山脉的山谷里,卡洛斯正带领一群村民翻越险峻山道。他们背着石板、凿具和种子,前往一处被遗忘的古村落遗址。那里曾因一场瘟疫被废弃,百年无人踏足,连地图上都已抹去它的名字。但昨夜,村中最年幼的女孩做了个梦??梦见一个穿旧棉袄的人站在枯井边,往井底放了一颗石子,然后对她说:“名字还在,家就还在。”
今晨,女孩醒来,手中握着一块蓝灰石子,裂纹中绿意盎然。
卡洛斯听后沉默良久,随即召集队伍。“我们去把那些名字找回来。”他说,“不只是为了死者,是为了活人还能记得自己是谁。”
他们在废墟中清理出一座倒塌的祠堂,将收集来的三百七十二个姓名一一刻在石板上。每刻完一个名字,就将一块石子埋入土中。当最后一块石子落下,荒芜的庭院竟冒出点点绿芽,野草破土而出,一株老槐树干裂的枝头也抽出新叶。
孩子们围着石碑跳舞,嘴里念着陌生的名字:“玛利亚……安东尼奥……小何塞……”
声音稚嫩,却庄重如誓。
而在北极圈内,因纽特村落的泉边,萨满正举行一年一度的“归名祭”。月圆之夜,全村人围坐泉畔,轮流呼唤祖先之名。今年不同的是,泉水中央浮现出一行字迹,由水汽凝成:
>“谢谢你们还记得我。”
全场寂静。
老萨满颤抖着站起,泪水滑落脸颊。“这不是幻觉……他们真的听见了。”
更远的南方,撒哈拉边缘的难民营里,阿米娜正教一群孩子画画。她的教室墙上挂着那幅“老人牵童走向太阳”的画,阳光透过帆布缝隙照进来,恰好落在画中老人的眼睛上,仿佛他在微笑。
一个小男孩怯生生举起手:“老师,如果没人记得我的名字怎么办?”
阿米娜蹲下身,轻轻握住他的手,将一块温润的石子放进他掌心。“只要你还愿意说出它,就永远有人在听。”她用手语比划,“就像春天总会来,哪怕雪还没化。”
男孩低头看着石子,忽然开口,声音沙哑却清晰:“我叫……伊布拉希姆。”
全班安静了一瞬,随即爆发出掌声。
有孩子哭了,也有孩子笑着跳起来喊他的名字。
窗外,沙漠上空再次飘下雪花,轻盈如絮,每一朵都似藏着低语。
太平洋渔村的梅园正值花期,粉白的花瓣随风旋舞,落在老妇人膝头的毛毯上。她已能拄拐行走,每日午后都坐在院中晒太阳。儿子不再出海,开了间小书店,取名“听风楼”,专收关于记忆、孤独与陪伴的书。书架最显眼处,放着一本泛黄的手抄本,封面写着《祥子行迹录》,扉页有一行娟秀小字:“愿世间再无未被听见的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