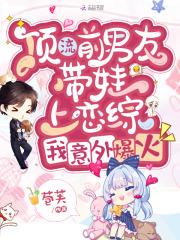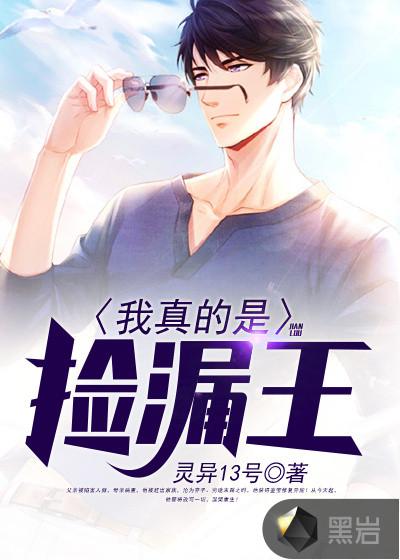笔趣阁>重生之我要拿下肖赛冠军 > 第145章 童年情景(第3页)
第145章 童年情景(第3页)
那种节奏外人听不见,也打断不了。
从那以后,我开始对他多看几眼。
不是好奇,更像是在确认,
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能这样与一架钢琴相处。
就像一般初次见面的孩子那样,
我们最初几次见面都显得有些笨拙。
他不太会寒暄,我也不擅长主动,
于是对话经常停在一句“嗯”或“是吗”上,
空气里静得能听见窗外的风吹过旧木窗。
可慢慢地,气氛就变了。
不知是因为熟悉了傅老师家的味道,
还是因为每周都要在那间屋子里碰见,
我们开始偶尔互相递谱,一起翻页,
甚至会在课后多留几分钟,闲聊几句无关紧要的话。
有一次我忘带节拍器,他从书包里拿出自己的那只,
递给我时小声说:“我调过,不会太快。”
那语气轻得几乎听不见,但让我记了很久。
之后我们常常会在傅老师家门口碰上。
他背着谱包,我提着琴袋,一前一后走下楼。
有时候路上遇到熟人打招呼,他只轻轻点头,
等那人走远后才小声问:“那是谁?”
我笑着告诉他,他就“哦”一声,再没别的。
我们的交流很简单,却也真切。
他说练琴太久会头疼,我告诉他要记得拉伸手腕;
我抱怨老师的课太严,他淡淡地说:“他教的是真东西。’
有时候我们也什么都不说,
只是并肩走过那段长长的走廊,
阳光从窗格里打进来,落在他的手上,
我能听见他手指轻敲谱袋的声音
节拍稳得像在心里弹琴。
就这样,我们一点点熟络起来。
从互相点头,到偶尔说笑,
再到能在长凳上安静坐半小时,
各自做自己的事,也不觉得尴尬。
后来我才明白,他之所以愿意和我说话,大概是因为我是他认识的人里,唯一一个能在琴上与他平起平坐的同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