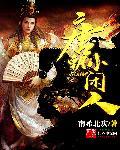笔趣阁>重生之我要拿下肖赛冠军 > 第151章 后续的日子(第4页)
第151章 后续的日子(第4页)
而是一种更深的控制,
他不允许自己被情绪打乱哪怕半拍。
而我不同。
我需要那种紧张,那种濒临失控的颤动,
就像需要呼吸。
只有那样,我才感觉自己还活着,
才知道音乐在血液里流动着,
是真实的。
他演奏的曲子是《悲怆》。
老实说,这首曲子大家实在听得太多了。
在全国比赛的舞台上,
它几乎成了某种安全的选择,
人人都熟悉,也人人都容易出错。
如果不能在里面弹出新的东西,
那就不过是一场平庸的模仿秀。
当唐老师听说他要选《悲怆》时,
当场皱了眉。
“这首曲子太老了,”
老师的语气里带着克制的无奈,
“要弹出自己的东西,不容易。”
可他只是沉默片刻,
轻声说:“我想试试。”
那句“试试”,不像任性,
更像是一种自觉的,安静的倔强。
老实讲,我那时并不看好这个选曲。
在那样的舞台上,
谁都知道华彩、技巧、气势更能取悦评委。
而他却偏偏选择了一首
被演到几乎失去神秘感的古典作品。
然而,当他坐上琴凳、
手指落下第一个和弦的那一刻,
我忽然意识到,
他弹的《悲怆》,
和我从小听过的所有版本都不一样。
那不是贝多芬的愤怒、
也不是表演者惯常的戏剧性冲突。
他的《悲怆》像是从一个极远的地方传来的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