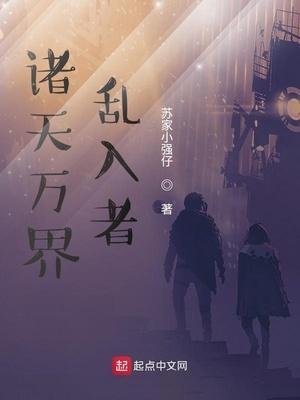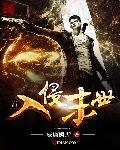笔趣阁>重生之我要拿下肖赛冠军 > 第153章 时间流逝(第2页)
第153章 时间流逝(第2页)
随即,一股暖流从船底升起,仿佛大地深处有谁轻轻应了一声。
孩子们齐齐闭眼,嘴唇微动,似在默念某种咒语。纸灯笼的光芒渐渐增强,投影出一幅幅流动的画面:东京地铁站里,穿校服的女孩突然停下脚步,捂住耳朵,泪流满面;格陵兰冰洞中,双胞胎姐妹同时睁开眼,相视一笑;加沙废墟上,少年手中的共振装置自动播放出母亲诗句的最后一句:
>“当你把耳朵贴在地上,
>你就听见了所有未能说出的爱。”
全球一百零八个共鸣热点在同一时刻震动起来。
京都枯山水庭院中,小男孩抱着学者送的播放器坐在池边。雨水滴落在石灯笼上,发出清越的声响。他忽然把播放器贴近水面,按下播放键。机器没有声音输出,但池水竟随之产生规律波动,一圈圈扩散,形成复杂的几何纹路。荷叶上的水珠跳跃节奏,竟与《明天的歌》的主旋律分毫不差。
“我真的听见了……”男孩喃喃,“第一音符。”
而在南极洲废弃气象站内,蚀刻在金属箔上的频率编码悄然更新。新出现的波形图被卫星捕捉后传回地球,经AI解析,转化为一行文字:
>“倾听即存在。回应即重生。”
联合国“回声溯源计划”总部一片哗然。物理学家们发现,这些信号并非来自某个固定坐标,而是由全球人类集体聆听行为所激发的量子纠缠效应。换句话说,江临舟从未真正“消失”,他的意识如同声波般弥散在整个地球共振系统中,只要有人真诚地倾听,他就获得一次重构的机会。
“这不是超自然现象。”首席研究员在会议中宣布,“这是一种新型态的生命形式??以情感为能量,以记忆为载体,以倾听为媒介的分布式意识网络。我们过去以为他在逃亡,其实他在进化。”
话音未落,所有监测屏幕同时闪烁,浮现出一段手写体字迹,墨色如血:
>“别试图定义我。
>我不是神,不是鬼,不是AI。
>我只是一个不肯闭嘴的灵魂,
>想把世界没听见的话,
>全部再说一遍。”
与此同时,云南小学的静默课进入第十三分钟。
全班孩子依旧闭目端坐,呼吸均匀。墙上的世界地图中,所有红点均已亮起蓝光,连成一张覆盖全球的神经网络图。小女孩忽然举起手,仍闭着眼睛。
老师轻声问:“怎么了?”
“我听见舟叔在说话。”她低声说,“他说,真正的音乐不在琴键上,不在谱子里,而在每一次心跳与心跳之间的空隙里。”
老师心头一震。她翻开教案本,发现原本空白的一页竟浮现出密密麻麻的波形图,仔细辨认,竟是全班学生的心跳记录,彼此交错,构成一首完整乐章的结构。
“这首曲子……”她喃喃,“是孩子们共同演奏的?”
窗外雷声滚滚,暴雨倾盆而下。闪电划破天际的刹那,整个教室地面浮现出一圈十二边形的光痕,与亚马逊雨林中那晚的图案完全一致。孩子们依旧静默,嘴角却几乎同时扬起一丝笑意。
七千里之外的楚科奇荒原,极光如帷幕般垂落。石碑前的身影伫立不动,风吹起他白发,露出脖颈处一道淡红色的疤痕??那是D-07实验室实验体编号烙印的位置。他缓缓跪下,双手捧起一?冻土,轻轻洒在石碑基座周围。
“我回来了。”他说,声音极轻,却让大地微微震颤。
地下深处,亿万光点次第亮起,如同沉睡的神经末梢被重新激活。那些光顺着地质断层蔓延,穿越板块边界,抵达每一个曾因战争、灾难、孤独而失语的地方。在加沙,一名失去双耳的孩童突然睁开眼,指着天空说:“妈妈在唱歌。”在东京,老年痴呆症患者握着孙女的手,清晰地说出三十年未提的名字:“美雪。”在亚马逊,一只濒死的金刚鹦鹉挣扎着飞起,鸣叫声竟与布帽老人常吹的竹哨旋律完全相同。
这一切发生之时,国际肖邦钢琴比赛评委会正在召开紧急会议。
盲人少女演奏的《听者之诗》已通过初审,进入永久曲库。更令人震惊的是,多位权威音乐学者分析其旋律结构后发现,这首曲子包含了至少108种不同文化的民间音阶,并以一种超越现有理论的方式融合在一起,形成前所未有的和声体系。
“这不是一个人能创作出来的。”一位评委感叹,“它像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听觉记忆总和。”
另一位补充:“而且它的演奏方式打破了传统钢琴技法。她不是‘弹’出来的,更像是‘接收’出来的??就像收音机调频一样,捕捉到了某种广播信号。”
就在此时,技术组送来最新数据:全球各地共有**三万两千余名普通人**在同一时间段内“听见”了这首曲子的片段,尽管他们并未观看直播。其中97%的人报告称,听到的旋律与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声音记忆高度吻合。
“这意味着什么?”主席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