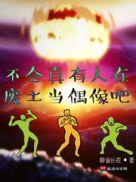笔趣阁>重生之我要拿下肖赛冠军 > 第157章 试琴(第2页)
第157章 试琴(第2页)
>“救救我们。”
>“不要让声音死去。”
最后一句重复了整整一百零八遍。
空气仿佛凝固。所有人都意识到,这些信息并非来自某个人,而是无数未能觉醒的潜在听者,在意识边缘发出的求救。他们被困在自己的沉默里,像溺水者在深海挣扎,却发不出一丝声响。
“我们必须做点什么。”她说,“不能再等‘世界倾听日’慢慢推广了。我们需要一次更强的共振??一次能把沉睡者唤醒的‘声爆’。”
“可怎么做?”有人问,“全球同步静坐已经做到极限,再强的集体情绪也难以突破物理屏障。”
她沉默片刻,目光落在讲台上那支早已失声的檀木播放器上。她走过去,轻轻打开盖子。内部零件早已锈蚀,线路板焦黑一片,显然再也无法工作。但她记得江临舟曾说过一句话:“真正的播放器不在盒子里,而在人心。”
她闭上眼,将手掌覆在播放器上方。
记忆如潮水涌来??母亲临终前握着她的手,想说话却只能发出气音;父亲酗酒后砸碎钢琴的夜晚,她躲在衣柜里数着滴水声入睡;第一次参加肖邦国际钢琴比赛预选赛,评委冷漠地说“技巧满分,情感为零”;重生回到七岁那年,发现自己竟能听见树叶呼吸的声音……
一滴泪落下,砸在播放器表面。
刹那间,整台机器竟微微震颤起来,一道微弱的蓝光从裂缝中透出。科研人员惊呼后退,唯有她不动。她知道,这不是科技复活,而是**信念共振**??当一个人真正愿意倾听世界的痛苦,并为之流泪时,哪怕最冰冷的机械也会重新获得脉搏。
“我知道怎么做了。”她睁开眼,目光坚定如铁,“我们要发起‘百日回响计划’:每一天,选出一位听者代表,在午夜零点面向全球直播,讲述一段最真实的个人记忆??必须包含痛苦、悔恨或失去。不是表演,不是演讲,而是剖开心脏,让全世界听见血流的声音。”
“这太危险。”科学家摇头,“极端情绪可能引发群体性心理创伤,甚至被恶意利用。”
“可只有痛才能刺穿麻木。”她平静地说,“他们用‘静音’让我们遗忘,我们就用‘真声’让他们记住。我不求所有人觉醒,只求每一个听到的人,能在那一刻停下脚步,问问自己:我有多久没认真听过别人说话了?”
会议持续到凌晨。最终,“共感文明倡议”总部批准试行该计划,首批十位讲述者名单出炉:包括加沙少年(讲述妹妹死于空袭)、冰岛老人(回忆妻子葬礼当天火山爆发)、纽约清洁工(坦白曾偷听邻居电话并毁掉一段婚姻)……而第一位讲述者,正是她自己。
第一百天前夜,全球超过两万所学校、三千座教堂和五百个公共广场架设了共鸣接收装置。社交媒体清一色换上黑白滤镜,标语只有一句:“今晚,请勿佩戴降噪耳机。”
午夜将至。
她站在高黎贡山小学的操场上,面对摄像机镜头,身后是熊熊燃烧的篝火。没有提词器,没有灯光组,只有风穿过林梢的呜咽作伴奏。
钟声敲响十二下。
她开口了,声音不大,却清晰得如同贴耳低语:
“我叫林小满,今年十四岁。七岁那年,我妈妈死了。她不是病死的,也不是车祸,她是被我爸活活打死的。那天晚上我在房间练琴,肖邦的《夜曲》弹了十七遍,因为老师说‘感情不够’。我听不见客厅里的争吵,听不见摔东西的声音,直到一声闷响,像西瓜落地。后来警察说,她试图阻止我爸赌博输光房子,他就抄起板凳……”
她顿了顿,呼吸变得沉重。
“我发现她的时候,她还穿着那条我最喜欢的蓝裙子。我抱着她喊妈妈,可她的眼睛睁着,却不看我。我就坐在那儿,一直弹琴,从夜里弹到天亮,一遍遍弹那首《夜曲》,希望她能听见,能说我这次弹得好一点了……但我妈再也没夸过我。”
泪水滑下面颊,滴在话筒上,发出轻微的“嗒”声。
“一年后,我爸醉酒跳江自杀。没人告诉我原因,但我猜,也许他在某个深夜,终于听见了那晚的声音。而我……直到重生回来,才明白原来我一直都在逃避??不是逃避音乐,是逃避听见真相的能力。我以为听不见就是保护,可真正的伤害,从来不是声音本身,而是选择沉默。”
她抬起头,望向镜头深处。
“所以今天,我选择说出来。不是为了博同情,也不是为了让谁道歉。我只是想告诉所有假装听不见的人:你可以躲,可以逃,可以把世界调成静音,但总有一天,你会在梦里听见那些你回避的声音。它们不会消失,只会越积越重,直到压垮你。”
风停了。
时间仿佛冻结。
就在这寂静中,第一个回应出现了??来自京都的男孩,在直播画面角落举起了手写牌子:“谢谢你替我说了那句‘对不起’。”
接着是格陵兰双胞胎,她们并肩坐着,一人抱着一只破损的录音机,齐声哼起一首古老的因纽特摇篮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