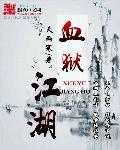笔趣阁>西游之浪浪山的金蟾子 > 第203章 金角银角 偷丹贼又来了(第2页)
第203章 金角银角 偷丹贼又来了(第2页)
陈砚甩开手,低声道:“我正因记得,才不能闭嘴。”
当晚,他偷偷潜入档案库,翻找旧卷。终于在一堆废纸中发现一本残册??竟是当年沈青禾呈上的《禁史残编》初稿誊本!纸页泛黄,边缘焦黑,显然曾遭火焚,但仍可辨识部分内容。其中一段赫然记载:
>“永昌三年,帝病重,权臣假诏立储,逼宫换嫡。时任御史中丞林知远察觉有异,欲上书谏言,却被‘缄口令’所困,喉结剧痛,血痰盈碗,终夜呕血而亡。其临终前所写奏章,今藏皇陵偏殿第三密格,题曰:《正统辩》。”
陈砚浑身颤抖。他知道,这才是真正的禁忌??不止是过去的罪行,更是当下权力合法性的根基。若此文现世,整个朝廷都将动摇。
他咬牙将残页藏入贴身衣袋,正欲离开,忽觉背后寒意袭来。转身一看,一名黑衣人立于阴影之中,手中捧着一面铜镜,镜面漆黑如墨。
“你想说?”那人声音空洞,“可你说了,谁信?谁听?谁敢信?”
陈砚后退一步:“你们……是‘缄默使’?”
黑衣人不答,只将铜镜缓缓抬起。镜中竟无倒影,反而浮现出无数张扭曲的脸??有哭的、笑的、呐喊的、沉默的……全是历代因言获罪者的魂魄,被困于镜中,永世不得超生。
“每一面缄默镜,囚禁百魂。”黑衣人道,“你若执迷不悟,下一面,就是你的脸。”
陈砚却不退反进,冷笑道:“你们以为,封住一个人的嘴,就能封住真相?可你们忘了??”他猛地掏出音籽,按在胸口,“**只要还有人愿意听,我们就永远有话可说。**”
音籽骤然发光,一道清音穿透虚空。刹那间,铜镜裂开一道细纹,一声凄厉哀嚎自镜中传出,黑衣人踉跄后退,化作黑烟消散。
陈砚瘫坐在地,冷汗淋漓。但他嘴角却扬起一抹笑。
他知道,自己已经踏上了那条无法回头的路。
三日后,一封匿名密信出现在阿篱案头。信中附着《正统辩》残篇抄录,并注明藏匿地点。末尾只有一句话:
>“林知远未死于病,而是被活活憋死在自己的真话里。
>我不愿做第二个他。”
阿篱读罢,久久不动。裴昭站在她身后,轻声问:“还查吗?这已触及龙骨,一旦揭开,不只是平反,而是改朝换代。”
“那就改。”阿篱终于开口,声音平静如雪,“若真相只能藏在地底,那这天下,本就不该存在。”
她召来七十二名最信任的守语人,亲自拟定“破镜计划”??目标:盗取《正统辩》原件,公之于众。
行动定在皇帝寿辰之夜。届时皇陵守卫调防,祭祀仪式繁复,正是混乱之机。
七名精锐使者乔装成礼官,混入祭队。他们携带特制“听骨罗盘”,可感应文字中的情绪残留。当队伍行至偏殿,罗盘指针剧烈转动,指向第三密格。
夜半子时,使者撬开暗格,取出一卷密封竹简。刚欲撤离,警铃骤响!数十名黑衣禁卫从四面杀出,手持缄默镜,封锁所有出口。
“放下圣物!”为首的禁卫统领怒喝,“此乃欺君大罪!”
一名女使者冷笑:“你们供奉的,才是真正的伪君。”
双方激战。音籽爆裂声此起彼伏,每一颗炸开,都释放出一段被压抑的呐喊。有孩童哭求不要被献祭,有妇人控诉夫死于冤狱,更有老臣临终嘶吼:“社稷危矣!无人肯言!”
混乱中,竹简被抛出殿外,落入接应之人手中。那人正是柳芸。她抱着竹简狂奔,铁链拖地,鲜血染红雪路。身后追兵紧逼,箭矢破空。
就在千钧一发之际,浪浪山方向,逆钟第三次鸣响。
无声。
可全城百姓,无论睡梦中还是醒着,脑海中同时响起一段话??
>“朕非正统,尔等皆知。
>只是无人敢说。
>今日有人说了,你们,听吗?”
那是林知远《正统辩》的开篇第一句,经由逆钟放大,直击人心。
刹那间,追兵停下脚步,有人跪地痛哭,有人撕毁腰牌,更有守城士兵主动打开城门,放柳芸出城。
天明时分,全文已在民间传开。书院学子集会朗诵,街头巷尾张贴全文,甚至连市井童谣都改了词:
>“金銮殿上坐的谁?
>不是真龙是傀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