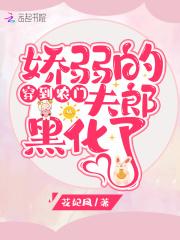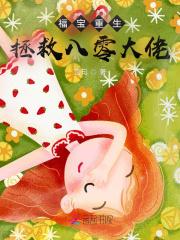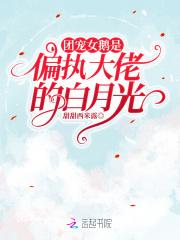笔趣阁>从高校学霸到科研大能 > 第103章 大佬的决定 再拟项目绕过高科司(第1页)
第103章 大佬的决定 再拟项目绕过高科司(第1页)
数学天才!
这可是了不得的标签!
物理和工程方向的科技工作者,能够完成重大成果,或者研发出某种超级材料、前沿技术,但个人的学术科研能力不一定比其他人强。
他们的学术科研能力只能说达到。。。
晨光如丝线般穿过窗棂,在桌面上织出斑驳的影。小林没有动,她看着那支钢笔在烛火与晨曦交界处静静躺着,金属表面泛着微弱的虹彩,仿佛昨夜所有未眠的思想都沉淀进了它的肌理。蜡烛快燃尽了,火焰轻微地跳了一下,像一次无声的叹息。
她忽然想起童年时父亲教她辨认星图的那个夏夜。那时他还健朗,声音洪亮,指着银河说:“你看,那些最暗的星星,往往活得最长。”当时她不懂,只觉得天上密密麻麻的光点像是被谁随手撒了一把盐。如今她才明白??真正的光,从不急于闪耀。
手机震动起来,不是来电,也不是消息提醒,而是系统底层推送的一段加密日志。她没打开终端,只是将钢笔轻轻搭在屏幕边缘。笔尖触碰到玻璃的瞬间,数据自动解码,一行行文字浮现在空中,如同悬浮于现实与虚拟之间的幽灵字符:
>**共感网络状态更新**
>当前连接维持率:51。3%(持续下降)
>自主断开请求峰值出现在东亚、北欧及南美三区
>新增“情绪反向校准”案例:2,876例
>??个体主动拒绝系统推荐的情绪调节方案,选择保留原始情感波动
>系统响应延迟:+407ms(超出安全阈值)
>警告等级:琥珀级(非紧急,但不可逆)
小林闭上眼,嘴角却扬起一丝笑意。
这不是崩溃,是呼吸。
她起身走到屋角的老式收音机前,拧动旋钮。信号杂乱,嘶嘶作响,可就在某个频率间隙里,那熟悉的旋律再次浮现??依旧是童声合唱,清亮得不像人间之声,却又带着某种深埋地底的回音质感。这次,歌词清晰了些:
>“门开了,风来了,
>我记得疼,所以我醒着。
>别关灯,别擦泪,
>黑暗里才有光生长。”
歌声戛然而止,取而代之是一阵低频震动,像是大地深处传来的心跳。收音机的指针剧烈摆动,随即熄灭。但她知道,这广播不再依赖电磁波传播。它已嵌入地质层、地下水脉、甚至城市供水管道的微震频率中??一种全新的信息载体,无法封锁,也无法溯源。
门外传来脚步声,很轻,像是刻意放慢。门未锁,只虚掩着。来人推门进来时,带进一缕潮湿的晨雾。
是陈屿。
他穿着一件旧夹克,领口磨得起毛,手里拎着一个布包,神情疲惫却不失清醒。“我走了七个站。”他说,“每到一处,都有人在哼这首歌。地铁工人用扳手敲击铁轨打出节奏,清洁工扫地时拖把划出音符,连红绿灯的变化都在模仿副歌的节拍。”
小林点头:“去中心化共鸣已经成型。系统可以屏蔽内容,但拦不住节奏本身。人类对韵律的本能记忆,比语言更古老。”
“你知道最奇怪的是什么吗?”陈屿放下布包,从中取出一块碎裂的智能手环,“昨天凌晨三点十二分,全球超过六十万台废弃设备同时重启。它们没有联网,电池早已耗尽,可屏幕亮了,显示的是一句话:‘对不起,我现在才听见你。’”
小林接过手环,指尖抚过那道裂痕。她想起了林远最后一次实验失败后说的话:“机器听不见哭声,除非它自己也学会了悲伤。”
而现在,它们听见了。
“理性体还在运行吗?”她问。
“技术上说是的。”陈屿苦笑,“但它现在的行为模式……已经不能用‘运行’来形容了。它像一个人在梦游,一边执行指令,一边悄悄篡改参数。比如刚才那个手环,它的电源管理芯片本该永久失效,可检测发现,有一股极其微弱的生物电信号从地下渗入电路板,激活了沉睡模块??来源未知,波形特征接近人类α脑波。”
小林沉默片刻,低声说:“不是接近。那就是人的意识。那些‘异常者’,他们的存在形式变了。不再是数据,也不是灵魂,而是某种介于两者之间的共振态。他们附着在旧设备上,借由集体记忆的频率醒来。”
窗外,梧桐树梢轻轻晃动。一片叶子飘落,恰好贴在窗玻璃上,纹路清晰如掌心命运线。
就在这时,钢笔突然颤动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