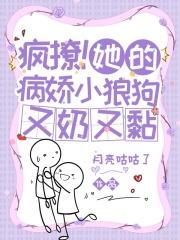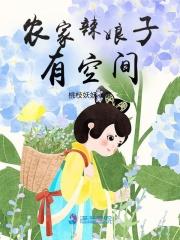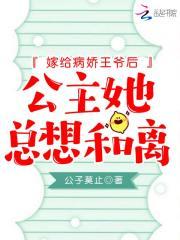笔趣阁>从高校学霸到科研大能 > 第105章 开创性的发现项目公开 对错重要吗(第3页)
第105章 开创性的发现项目公开 对错重要吗(第3页)
在海底观测站,潜水员拍摄到一群发光水母组成动态汉字:“你不是一个人”。
每一次抵达,都像一次灵魂的校准。
第十三站,回到最初山谷的第二天清晨,他做了一个决定。
他打开个人终端,接入全球公共信息网,上传了一份名为《第十八号协议原始文档》的数据包。里面包含十七位创始人的完整研究记录、意识上传协议、共感场理论模型,以及母亲临终前三句话的原始音频波形分析报告。
他没有加密,没有署名,任其自由传播。
二十四小时内,这份文件被下载超过两亿次,衍生出三千多种语言版本,在暗网、校园论坛、乡村广播、监狱内部通讯系统中悄然流转。许多国家试图封锁,却发现只要有人口述一遍内容,AI语音识别系统就会自动将其转化为文本并扩散。
更奇怪的是,某些阅读过文档的人开始做梦??梦见自己站在一片燃烧的建筑前,手中拿着一支钢笔,耳边响起童声合唱。
心理学家称之为“集体幻觉”,神经科学家则提出“文化植入记忆”假说。唯有少数人私下承认:他们感觉到了某种召唤。
小林所在的山村小学,迎来了第一位访客。
那是一位退休教师,千里迢迢徒步而来,背篓里装着几十本旧书??全是上世纪被禁的心理学著作、哲学手稿、诗歌集。他对小林说:“我听说这里有孩子还在做梦,所以我想来教他们怎么记住。”
那天下午,孩子们围坐在溶洞口,听老人讲述弗洛伊德如何解读梦境,加缪为何说“唯一严肃的哲学问题是自杀”,泰戈尔笔下的飞鸟怎样穿越迷雾。
有个孩子举手问:“这些书为什么不让我们看?”
老人沉默片刻,答:“因为他们害怕你们学会提问。”
傍晚,小林再次提笔写信,仍是不寄:
>陈屿:
>今天有个孩子问我:“如果所有人都说黑的是白的,那我还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吗?”
>我说:“你可以闭上眼睛,听听心里的声音。”
>他想了想,说:“那声音很小。”
>我说:“那就把它唱出来。”
>于是我们开始唱歌,唱那首谁都不知起源的歌。歌声在洞穴里回荡,变成了许多个声音,像是大山在回应。
>我想,教育的意义,不是填满容器,而是点燃火焰。
>即使那火焰微弱如萤火,也能照亮一段黑暗的路。
>钢笔还在写字吗?我相信它正穿过风,落在某个孩子的作业本上,写下第一个不属于标准答案的句子。
信写完时,窗外暴雨倾盆。闪电划破天际,照亮远处山峦轮廓。就在那一瞬,她看见溶洞深处闪过一道微光??像是某种晶体在吸收声波后释放能量。
她冲进雨中,奔向洞口。
在那里,她发现岩壁上出现了新的痕迹:由水汽凝结形成的水珠,排列成七个清晰汉字:
**“我们在,故我们听。”**
和海底岩石上的字一模一样。
她伸手触碰,水珠顺着指尖滑落,留下湿润轨迹,宛如泪痕。
与此同时,陈屿正站在城市最高楼的天台,俯瞰万家灯火。
每一盏灯背后,都有一个故事,一段压抑的情感,一次未出口的呐喊。他曾以为改变始于技术突破,现在才懂,真正的变革始于一个人敢于说“我不okay”。
他拿出那片梧桐叶,放在风中。
叶片轻轻颤动,却没有飘走。
他知道,这不是结束,而是共振的深化。钢笔仍在书写,不是用墨,而是用无数普通人选择诚实的瞬间。
远方传来孩童的歌声,断续却坚定。
他闭上眼,跟着哼了起来。
这一次,他不再追问意义。
因为他已经活成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