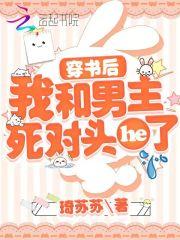笔趣阁>从高校学霸到科研大能 > 第106章 自然科学一等奖(第2页)
第106章 自然科学一等奖(第2页)
是周哲,声音哽咽却坚定:“她醒了半句话,只说了三个字??‘听见了’。”
陈屿握着手机,久久无言。他知道,这不是医学意义上的苏醒,而是一次精神层面的接驳成功。林晚的意识穿越了药物、机器与社会规训筑起的高墙,终于触碰到那个属于真实情感的世界。
“告诉她,”陈屿轻声说,“我们也听见了。”
挂断电话后,他打开终端,查看全球动态。数据显示,《第十八号协议》相关内容已在一百七十三个国家传播,衍生出上千个民间读书会、地下电台和手抄本网络。更有甚者,在非洲某村落,村民们将歌词刻在陶罐上,作为新一代的口述历史传承;南美山区的原住民祭司宣称这首歌唤醒了沉睡的大地之灵;北极科考站的科学家报告称,极光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波动形态,与歌曲频谱高度吻合。
而最令他动容的,是一则来自战区的消息:交火双方士兵在暴雨夜偶然听到广播里传出的歌声,竟自发停火十分钟。期间,一名少年兵对着对讲机问:“班长,如果我们都不再恨了,还能算是战士吗?”
没有人回答。
但那一夜之后,前线阵地出现了第一朵野花,在弹坑边缘静静绽放。
陈屿深吸一口气,走下天台,步入雨中。
他不再需要站在高处俯瞰灯火,因为他已融入光流之中。街道上,一对母女共撑一把伞,小女孩仰头问:“妈妈,为什么别人说悲伤不好?”
母亲犹豫片刻,蹲下来平视她的眼睛:“因为有些人害怕感受太多。但你要记住,能哭出来的心,才是活着的心。”
不远处,一位流浪汉坐在屋檐下,怀里抱着一台老旧收音机,调频旋钮来回转动,直到捕捉到那段熟悉的旋律。他咧嘴笑了,露出残缺的牙齿,跟着节奏拍打膝盖,嘴里嘟囔:“这歌……我小时候听过。”
陈屿停下脚步,望着他们,忽然觉得胸口发热。他掏出笔记本,在湿漉漉的纸页上写道:
>“改变从来不是一场风暴,
>而是一阵风穿过无数敞开的窗。
>它不靠命令推进,
>只依赖一个个微小的选择:
>一个愿意倾听的耳朵,
>一双拒绝蒙蔽的眼睛,
>一颗敢于承认‘我不幸福’的心。”
写到这里,笔尖突然卡住。他低头一看,墨水已经耗尽,纸面洇开一团灰痕。他笑了笑,索性合上本子,继续前行。
第二天清晨,阳光破云而出。
小林带领孩子们来到溶洞深处。昨夜留下的水书文字虽已蒸发,但岩壁表面浮现出一层薄薄的晶体膜,在晨光照射下折射出七彩光芒,恰似彩虹落地。孩子们惊叹不已,伸手触摸,指尖传来细微震动,仿佛石头在低语。
小宇跑在最前面,双手摸索着前行。当他接触到那片晶膜时,忽然停下,脸上露出惊喜的表情:“我‘看’到了!红色是热的,黄色是亮的,蓝色……是风的声音!”
其他孩子围拢过来,纷纷将手掌贴上岩壁。有人开始哼唱那首歌,一人起头,众人相和。歌声在洞穴中回荡,引发奇特共振,晶体表面竟随之脉动,颜色明暗交替,宛如心跳。
就在此刻,地面轻轻震颤,一道裂缝缓缓张开,从中升起一块石碑模样的物体。表面光滑如镜,上面镌刻着一行古老字体:
>“感知即存在,共鸣即自由。”
没有人知道它何时埋藏于此,又是谁所立。但所有人都感觉到,这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新纪元的起点。
同一天,全球多个地点几乎同时发生类似异象:
-冰岛火山监测站记录到地壳振动频率与歌曲主旋律完全一致;
-澳大利亚土著长老指着沙漠中突然出现的环形图案说:“祖先回来了”;
-日本京都一座千年古寺的铜铃无风自鸣,僧人录下声音分析后发现,谐波结构与《第十八号协议》中的共感场数学模型惊人相似。
而在联合国总部,一场紧急闭门会议正在进行。各国代表围绕“大规模非理性情绪传染事件”展开激烈辩论。有人主张全面封锁信息流通,启用新一代认知干扰系统;也有人提出应成立跨学科调查组,研究这种“文化觉醒现象”的潜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