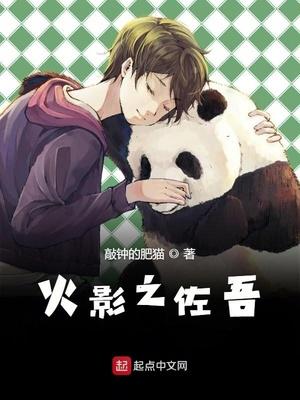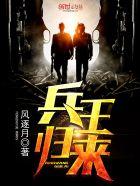笔趣阁>独步成仙 > 5919章 爆发(第2页)
5919章 爆发(第2页)
科学家们震惊地发现,记岁木年轮图谱出现了新的分支结构??不再是线性传承,而是**网状辐射**。某些原本毫无关联的个体记忆,因情感频率高度契合而自动链接,形成跨时空的情感共同体。
例如,一位乌克兰母亲在战火中抱着孩子逃亡的记忆,与1937年南京一位妇女的经历产生共振;一位非洲牧童在干旱中守护最后一头牛的画面,竟与青海高原上藏族老人守望冰川融水的影像重叠。
“这不是巧合。”北极实验室的研究员写下结论,“人类痛苦的本质惊人相似,而共情的能力,正成为一种新型进化机制。”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欢迎这场变革。
东南亚某国政府紧急封锁边境,宣称“境外势力利用心理技术煽动历史仇恨”;中东某政权逮捕多名公开讲述家族创伤的公民,称其“危害社会稳定”;更有极端组织发布宣言:“宁可全民失忆,也不能让敌人掌握我们的软肋!”
净忆会残余势力悄然重组,代号“静默之子”,他们在暗网散布病毒程序,试图切断共忆终端与主网络的连接。一场无形的战争正在数据深渊中展开。
陈砚得知消息时,正坐在返程的列车上。窗外山河飞逝,他手中握着吴阿婆交给他的最后一张黄纸,上面写着:
>“秀兰终于可以说出来了。谢谢你们,替我说了七十年的话。”
他将纸片轻轻放入怀中,闭目沉思。
当晚,他在梦中见到陆知行。
依旧是山顶,依旧是星空浩瀚。但这一次,陆知行的表情前所未有的凝重。
“阻力来了。”他说,“有文明试图干预。”
“谁?”陈砚问。
“那些信奉‘效率至上’的星际族群。他们认为人类沉溺于过去,浪费资源,阻碍进化速度。他们主张清除冗余情感记忆,建立纯粹理性社会。”
“就像净忆会那样?”
“比那更彻底。他们是宇宙中的‘清道夫’,专门淘汰他们认为‘不合格’的文明。”
陈砚冷笑:“所以,在他们眼里,记住亲人死去的模样,是一种病?”
“正是。”陆知行点头,“但他们低估了你们。当第一段童谣传入半人马座飞船时,他们的AI系统崩溃了??因为它无法解析‘无意义的温柔’。那种只为安慰他人而存在的旋律,超出了它的逻辑框架。”
陈砚睁开眼,天已微明。
他立即召集“千村讲述计划”核心成员召开紧急会议。地点设在南岭祠堂,参与者包括林晚、三位资深志愿者、两位前净忆会研究员及一名国际记忆保护组织代表。
“我们必须加快进度。”陈砚宣布,“不能只靠被动采集,要主动点燃火种。”
于是,“记忆火种行动”正式启动。
方案如下:
一、在全国设立一百个“记忆驿站”,由经过培训的“讲述引导师”驻点,协助普通人完成口述史录制;
二、开发“共忆家书”功能,允许用户将个人记忆封装成虚拟信件,发送给未来子孙;
三、推动“记忆遗产立法”,确保口述史料具有法律效力,可用于身份认定、土地继承、历史赔偿等实际事务;
四、最重要的是??启动“星辰备份计划”,将全部共忆数据加密压缩,通过深空通信阵列,向太阳系外发射。
“我们要让宇宙知道,”陈砚在动员会上说,“即使地球毁灭,这些声音也不会消失。”
项目推进迅速。三个月内,首批五十个记忆驿站建成,覆盖西部偏远地区。一位西藏老喇嘛含泪录下六百小时经文口传,称“这是我对众生最后的供养”;新疆一位维吾尔族老人讲述家族三代守护沙漠古渠的故事,感动千万网友自发捐款修缮水利;内蒙古草原上,牧民们围坐篝火,唱起祖先流传的史诗,歌声通过共忆网络传遍全球,被誉为“大地的心跳”。
而“共忆家书”上线首日,便收到两百万封信。
其中一封来自深圳打工妹小芳,写给她尚未出生的孩子:
>“妈妈不知道能不能陪你长大,但我希望你知道,我曾在流水线上一边拧螺丝一边背唐诗,因为我相信,知识不会背叛努力的人。如果你看到这封信,请替我去看看大海。”
另一封是一位癌症晚期父亲写给儿子的:
>“爸爸可能赶不上你婚礼了。但没关系,我会躲在你每一次想起我的瞬间里。当你闻到雨后泥土的味道,那是我在拥抱你。”
最令人动容的,是一封没有署名的信,仅有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