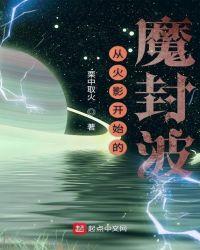笔趣阁>天唐锦绣 > 第二二零玖章 神兵天降(第1页)
第二二零玖章 神兵天降(第1页)
两河流域有着可媲美华夏之悠久历史,只是与华夏文明传承不绝不同,这里在历史中先后被多支异族所侵略、征服,古埃及、波斯帝国、罗马帝国、大食帝国……
所导致的后果不仅政权在于更迭,更严重是彻底掘断了两。。。
夜雨初歇,长安城外的听心坊檐角还挂着水珠,一滴一滴落进石阶前的铜盆里,发出清越的回响。坊内灯火未熄,值守的倾听使正将今日收集的三百七十二片陶片逐一编号归档。其中一片边缘焦黑、布满裂纹,像是曾被火燎过又勉强拼合而成。年轻学徒皱眉:“这又是哪个疯癫人烧了家书来投?”
老执事却不语,只将其轻轻放入共振盘。音波激发三息后,屏幕上浮现出断续文字:
>“我写了七十封信,没人拆开。
>我站在衙门前喊了三天,守卫说我扰民。
>最后我把信烧了,灰烬混着血咽下去……可我还是想说??
>那年修渠,死了三十六个民夫,名字全刻在崖底石头上。官报却写‘无伤亡’。
>你们看不见字,是因为它被泥浆盖住了。
>可我能听见他们在地下说话,每晚都在喊冷。”
老执事的手微微发抖。他认得这种笔迹??十年前陇西大旱时,有个独臂老农每日跪在驿道边递状纸,后来被人拖走,再没出现。系统查籍显示:此人姓陈,原为水利工程监工副手,因上报虚耗粮款遭贬黜,妻儿饿死途中,本人自此流落山野,户籍注销。
“不是疯癫。”老执事低声道,“是真相太重,常人背不动。”
他立即启动“沉声追溯”程序,调取过去二十年全国水利工程档案交叉比对。不出五日,果然发现一处疑点:秦州青岗岭引水渠竣工记录中,确有“岩层稳固,施工顺利”八字评语,但同期地方志提及“暴雨塌方,役卒多殁”,且当年秋赋骤减三成。更令人震惊的是,在AI深度解析下,一份看似正常的工程图纸背面,竟隐藏着微缩铭文??那是用特制药水书写、需特定频率光照才能显现的秘密名单,三十六个名字赫然在列。
消息上报当夜,太子亲自召见老执事。殿中烛火摇曳,他盯着那份复原名单看了良久,忽然问:“这些人的家属,还活着吗?”
“查到了七个后代。”老执事答,“最远迁至岭南,靠织麻为生;最近的就在城南菜市,卖豆腐。”
太子沉默片刻,起身走到窗前。月光洒在御园那株新栽的玉竹上,枝叶轻颤,似有低鸣。“我们总以为太平盛世,便无需再听哭声。”他说,“可原来有些眼泪,早已渗进地底,连风都吹不起来。”
次日早朝,太子奏请重审旧案,并提议设立“亡者之声”专项听证会,邀请所有疑似冤殁者的亲属入宫陈述。皇帝准奏,唯加一句:“不必拘礼法,让他们怎么说都行。”
于是七日后,紫宸殿改作听心堂。七位遗属依次登台。有人捧着残破衣角,说是父亲最后穿的袄子;有人抱着一块焦石,声称是兄长埋骨处挖出;最年幼者不过十一岁女童,跪在地上展开一幅炭笔画:一群人在黑暗隧道中牵手前行,领头那人回头微笑,手里举着半截蜡烛。
全场寂静。
太子命人将画悬于殿梁,随即宣布:即日起彻查历代积压工程案卷,凡涉及瞒报伤亡者,无论主官是否在世,皆追责到底;同时拨款修建“默念碑林”,将已知无名死者姓名一一镌刻其上,供后人凭吊。
此事震动朝野。有御史弹劾太子“以情乱法”,认为追查陈年旧账徒增动荡。太子当庭反问:“若法不能还魂以名,安能称其为公?”遂不再辩,唯取出一只梦铃置于案头,轻摇一下。铃声清越,绕梁不绝。他道:“诸位大人日日议政,可曾听过地底三十六人临终前最后一口气?”
无人应答。
风波未平,江南又起涟漪。
苏州听心坊接到一封匿名信,内附半页残诗:
>“月照千江不见底,
>舟沉不闻桨声起。
>若问冤魂何处归?
>桥下青苔皆姓李。”
经查,此诗出自贞观十九年一位被贬文士之手,其人因谏言触怒权贵,流放途中溺亡太湖。而所谓“桥下青苔”,实指姑苏枫桥畔一段隐秘水道??据当地渔民世代口传,每逢阴雨,河面便会浮现数十具绑缚石块的尸骸影子,随波沉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