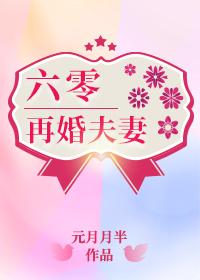笔趣阁>我写的自传不可能是悲剧 > 第六百一十八章 外面多贵啊(第3页)
第六百一十八章 外面多贵啊(第3页)
“那怎么办?”我问。
他笑了:“那就让他们亲眼看看‘有用’长什么样子。”
次日清晨,一封公开信出现在所有联网设备首页,署名是**所有曾留下一句话的人**。
信中没有辩论,没有煽情,只有一串坐标链接。点击后,用户会被引导至一段实时影像:
画面中是一位癌症晚期的女孩,躺在病床上,手里握着一支发光的笔。她正在写:“我想看看明年春天的樱花。”
下一秒,窗外突然飘起粉色花瓣??并非实物,而是由无人机群组成的光影投影,在城市上空缓缓绽放。与此同时,全球二十四座城市的公园同步开启樱花灯光秀,持续整整七天。
这不是预录视频,而是真正的联动响应。
因为就在三天前,已有超过八百万用户在共写平台上标记同一愿望:“让小安看见樱花。”
系统识别到情感密度突破阈值,自动激活了“现实编织协议”。
舆论瞬间反转。
有人哭着说:“原来我们真的能一起做点什么。”
有人开始自发收集“未完成的愿望清单”,发动社区力量逐一实现。
一位老人许愿“再听一次亡妻唱的那首老歌”,结果全市公交广播在同一天傍晚播放了那段录音,司机们默默调高音量,乘客们安静聆听。
审查者的攻击逐渐减弱。
不是被击败,而是被绕开。
就像黑暗无法战胜光明,只能在光到来时悄然退场。
一年后,国际共写联盟成立,总部设在原福建山村遗址。那里建起一座透明穹顶图书馆,收藏着迄今为止所有被留下的“一句话”。每晚八点,馆外墙体会投影当日最受欢迎的讲述,供路人驻足阅读。
我去参观那天,正巧看到一面墙在播放:
>“爸,我知道你打我是因为你害怕。我现在也当爸了,终于懂了。咱们和好吧。”
下面附着一行小字:此话由张先生于三年前留下。昨日,他父亲去世前握着他的手,说了平生第一句“对不起”。
我站在人群中,听见身后一个小女孩问妈妈:“如果我说了真心话,真的人家就会变好吗?”
妈妈蹲下来,指着墙上另一句话:“你看那边,那个人说他害怕上学,结果第二天全班同学都画了笑脸送他。有时候,一句话就像一颗种子,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开花,但只要你种下去,总有人会闻到香味。”
我默默离开,走向村外那片桃林。
树下坐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低头画画。我走近一看,是他用蜡笔在纸上涂鸦:一个大人牵着小孩的手,走在彩虹桥上,头顶写着歪歪扭扭的字:
>“长大以后,我要成为一个敢说‘我爱你’的人。”
我笑了笑,在他身边坐下:“画得真好。”
他抬头看我,忽然问:“你是那个守门人吗?”
我愣了一下:“谁告诉你的?”
“奶奶说的。她说你是最早写下第一个字的人,所以现在每个人都能安心说话了。”
我摇头:“我不是守门人。我只是第一个不肯关门的人。”
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然后递给我一支蓝色蜡笔:“那你帮我写一句吧?我想留给未来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