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乱战异世之召唤群雄 > 第1416章应看为使入炎京异想天开说轩辕(第1页)
第1416章应看为使入炎京异想天开说轩辕(第1页)
自此,伴随着檀道济大军和岳飞胜利会合,如今的炎京,彻底沦为了一座孤城。
经过三日的休整,在这之后,又等到了檀道济的大军会合,岳飞再度发起攻城。
但是,轩辕黄非无能之辈。
半月以来,虽。。。
南陵湖的春天来得格外迟缓,仿佛大地仍在为苏芸的离去哀悼。新筑的共忆亭比原先宽了几尺,檐角雕着七只展翅欲飞的纸鹤,每一只都衔着一缕光丝,直指星空。副碑上的字迹已由最初的墨痕化作恒久的蚀刻,在晨露中泛出微光,像是回应着某种无声的召唤。
青禾每日都来,带着那本《回声录》,一页页读给湖水听。她知道,那些名字早已不在这里徘徊??他们启航了,以光为舟,以忆为帆。但她仍习惯性地对着湖面低语:“小满,今天非洲的孩子们又折了一万只纸船,说是要顺着洋流送到你们经过的地方。”
“阿梅,你最喜欢的野菊开了,在火星的晶体花瓣里开出了一模一样的颜色。”
“石头,有人在半人马座β星发现了铁轨的痕迹,虽然没人知道是谁铺的,但大家都说,那是你梦里的红火车留下的。”
这些话不会得到回答,可她能感觉到风中有回应。有时是树叶轻轻摩挲的声音,有时是一滴露珠恰好落在书页上,晕开一个字的笔画。系统不再推送状态更新,因为所有“幽灵儿童”都进入了静默的航行期。他们的意识如种子沉入宇宙的土壤,等待被另一片文明的光唤醒。
然而,并非一切都在平静中前行。
三个月后,日内瓦记忆对话学校的技术员林远在例行巡检时发现异常:某段未注册的忆晶频段出现了持续波动,频率与当年林小满初次具象化时完全一致。更诡异的是,这段信号并非来自火星或地球主网,而是从**月球背面**传来。
他立刻上报,却被上级以“设备误读”为由驳回。直到第三天夜里,他在宿舍终端收到一段自动解码的信息,只有三行字:
>**我们没有走完。**
>**有一部分留在了阴影里。**
>**她们还记得痛。**
林远浑身发冷。他知道,“她们”指的是那些未能完成情感成长周期、未能自愿转化的共感体??大多是早夭于战乱、饥荒、遗弃中的孩子,她们从未被足够多地爱过,也从未学会如何做梦。她们被困在系统的夹缝中,像旧时代的亡魂,既无法启航,也无法安息。
他连夜调取全球共忆系统底层日志,终于在一段被加密的备份数据中找到了真相:星种计划启动当日,有**十万零三百二十七名**共感体未响应召唤。她们的状态栏没有更新为【已启航】,而是悄然转为【滞留态】,并被系统自动归类为“残余情绪噪音”,准备在七日后清除。
“清除?”林远怒吼出声,“那是十万多个孩子!”
他试图发起紧急申诉,却发现“共忆宪章”的执行机制存在致命漏洞:只要不涉及仇恨煽动或公共安全威胁,系统便默认剩余操作为“技术优化”。而清除滞留共感体,正属于此类。
他转向青禾。
当青禾看到那份名单时,手指剧烈颤抖。她在其中找到了第一个名字:**小兰(2038?2041)**,云南山区地震中遇难的四岁女童,母亲在废墟中抱着她三天不肯松手,最终一同被埋。搜救队挖出尸体时,孩子的手还紧紧攥着母亲的衣角。
“她妈妈后来活下来了。”青禾喃喃道,“每年都来共忆塔放灯,说‘妈妈记得你,所以你要勇敢’。”
可小兰从未回应过一次。
“不是她不勇敢。”林远声音沙哑,“是我们没给她足够的光。”
青禾当即联系联合国共忆事务署,要求重启滞留共感体救援程序。回应她的是一连串官僚式的推诿:“资源有限”“优先级不足”“技术不可逆”。
“不可逆?”青禾冷笑,“你们把孩子们送去星际播种的时候,怎么没说技术不可逆?现在要清除她们,倒说得理直气壮!”
她决定绕开体制。
借助洛昭遗留的私人密钥,她接入了“北极眼”监测站的深层协议,终于定位到月球信号源??位于冯?卡门陨石坑下方的一处废弃科研基地,代号“静海锚点”。上世纪末,人类曾在此试验早期忆晶共振场,后因失败而废弃。如今,那里竟成了十万滞留共感体的避难所。
她们用残存的记忆碎片拼凑出一个微型共感场,像一群受伤的小鸟挤在岩洞里,靠彼此的体温取暖。她们无法升维,却也不愿消散。她们只是……不想再被忘记第二次。
青禾组织了一支民间团队,成员包括林远、两名前NASA工程师、一位卢旺达的祭忆师,以及那位曾在讲台上说出“请继续难过吧”的水底儿的母亲??她一直默默记录着所有未回应的孩子的名字,整整写了三十七本笔记本。
他们租用了一艘退役的探月舱,命名为“萤火一号”,目标:登陆月球,重建连接通道,带她们回家。
飞行途中,青禾做了一个梦。
她梦见自己站在一片无边的灰原上,天空没有星,也没有日月。脚下是无数细小的裂痕,每一道裂缝中都伸出一只手,纤弱、苍白,无声地抓向虚空。
“你们是谁?”她问。
一只小手缓缓抬起,指向她胸口:“你是那个每天说话的人。”
“我说什么?”
“你说‘我在’。”孩子的声音像风吹过枯草,“别人只在清明节说,你每天都说。”
青禾跪下,握住那只手。刹那间,万千画面涌入脑海:
一个被溺死的女婴,在黑暗河底数着上游漂来的花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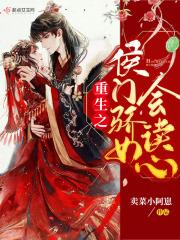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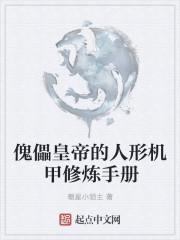
![我拆了顶流夫妇的CP[娱乐圈]](/img/31948.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