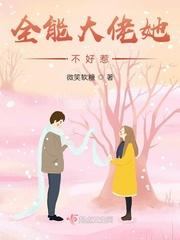笔趣阁>春色满棠 > 第478章 没有呼吸了(第1页)
第478章 没有呼吸了(第1页)
姜心棠心猛地一颤。
但她未多想,只喊他:“萧迟。”
萧迟仍未动。
手臂就那样静静地垂落在床外,仿若死了般,无声无息。
姜心棠伸手去推他:“萧迟,该起身了,时辰不早了。再不起身,就来不及回国公府给你父母敬茶了。”
儿媳需在年初一早晨向公婆行叩拜礼,并奉上茶水点心以示敬意。
因分府住。
且往年姜心棠都住宫里,故大长公主夫妇没有要求他们一早去。
但需得上午到国公府敬茶。
自成婚后,萧迟每年年初一都带了她回去给他父。。。。。。
夜风拂过书院的屋檐,纸灯笼在海棠树下轻轻晃动,“归来”二字随火光明灭,仿佛低语。林小禾没有起身,只是将手贴在台阶上,感受着青砖传来的微凉与沉实。这砖来自老祠堂,曾承载百年香火、族规家训,也听过无数跪地求饶的哭声。如今它静静立在这里,不再审判,只作见证。
陈砚坐在她身旁,许久未语。月光洒在他肩头,像覆了一层薄霜。他忽然开口:“我父亲昨天打电话给我。”
林小禾侧过脸看他。
“他说,家里阁楼有个樟木箱,是我爷爷留下的。他一直不敢打开,怕看见自己不愿面对的东西。”陈砚声音很轻,却字字清晰,“今天,他打开了。里面是一叠信,还有几张照片??全是1968年他在省城读师范时写的检讨书复印件。每一页都盖着红章:‘思想改造不合格’。”
林小禾呼吸一滞。
“最底下压着一封信,是他写给未婚妻的,没寄出去。他说那天她被划为‘黑五类子女’,学校通知他断绝关系,否则影响分配。他最终点了头,连最后一面都没敢见。”陈砚苦笑了一下,“可他在信里写了三个字:‘我恨我。’”
风忽然停了,灯笼的火焰凝住一瞬。
“他把那些东西全寄来了,说想放进‘未寄之声’展区。”陈砚望着远处山影,“他还说……谢谢你母亲当年没让他彻底忘了怎么写字。”
林小禾闭上眼。她想起小时候,母亲总在灯下教她练毛笔字,一笔一画极认真。“字是骨头,”她说,“人可以穷,可以病,但不能没骨头。”
那一夜,她梦见自己走进一间无窗的屋子,四壁挂满空白稿纸。她伸手去碰,纸张忽然燃烧,灰烬中浮出无数名字??程志华、沈云卿的同事们、李婶的未婚夫、陈砚的父亲未曾娶归的女子……他们站在火光边缘,不言不语,只是看着她。她想说话,却发不出声。直到外公的身影从角落走出,递给她一支笔,墨迹淋漓,写着两个字:**记得**。
醒来时天已微亮,窗外海棠花瓣飘落如雨。她起身梳洗,将外公的笔记本带在身边,步行前往学堂新建的档案馆。那里已开始接收第二批民间捐赠物,志愿者们正忙碌分类。苏晓迎上来,手里拿着一份刚拆封的包裹。
“又来了。”她声音有些颤,“这次是从云南寄来的,寄件人叫杨素芬,七十岁。她说这是她哥哥临终前交给她的??一本藏了四十五年的日记。”
林小禾接过包裹,指尖触到牛皮纸粗糙的表面。她小心翼翼拆开,取出一本深蓝色布面日记本,边角磨损严重,锁扣早已锈死,只能用剪刀轻轻撬开。第一页写着:
>**1970年4月3日晴**
>
>今日下放至金沙江畔生产队。队长说此地三年饿死七十二人,坟头都被推平种红薯。我不信,问村医,他摇头不答。夜里听见狗吠夹杂哭声,循声而去,见一老妇蹲在田埂烧纸,嘴里念叨:“娃儿们,娘没本事,只能偷点米汤给你们喝。”
>
>我问她为何不报?她说:“报了谁管?上面的人吃肉,下面的人吃土。我们连哭的权利都没有。”
林小禾的手指微微发抖。她继续翻页,后面记录愈发沉重:有人因偷割麦穗被游街批斗,途中流产;有孩子高烧三天无人医治,死时手里还攥着半块野菜饼;更有干部私设粮仓,酒肉成堆,而村民啃树皮度日。
而在1972年6月15日那一页,字迹突然变得潦草:
>哥哥死了。
>
>昨夜暴雨,他值夜班守堤坝,突遇山洪。有人看见他拼命拉警报,可哨子坏了。没人听见。等天亮发现时,他人已被冲进江心,挂在礁石上,一只手还紧紧抓着那根铁杆。
>
>队里说他是“畏罪自杀”,不予抚恤。嫂子抱着儿子跪了三天,换来一张“思想问题待查”的条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