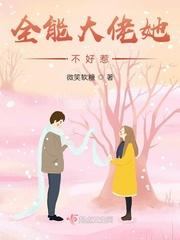笔趣阁>春色满棠 > 第478章 没有呼吸了(第2页)
第478章 没有呼吸了(第2页)
>我今晨偷偷把他埋在后山槐树下,没立碑。只在他衣袋里塞了这张纸条:
>
>“你没错。错的是不让好人发声的时代。”
泪水滴落在纸上,晕开墨迹。林小禾抬起头,看见苏晓也在抹泪。
“要不要联系这位杨素芬?”苏晓问。
“要。”林小禾深吸一口气,“不仅联系,我要亲自去一趟云南。如果她愿意,我想听她亲口讲完这个故事。”
当天下午,申请获批。与此同时,“言种计划”二期正式启动招生,十个试点学校陆续传来回音。甘肃一所中学的校长写道:“我们这里的孩子祖辈多为知青或下放户,家中禁忌重重。现在终于有人愿意听他们说话了。”广西某村小教师附上一段录音:十几个学生围坐一圈,轮流讲述爷爷奶奶从不提起的往事,说到动情处,几个孩子抱头痛哭。
林小禾听完整段录音,久久沉默。她忽然意识到,这些孩子不是在学习历史,而是在找回自己的身份。他们曾以为父母的沉默是冷漠,祖辈的回避是遗忘,殊不知那是伤得太深,怕疼到下一代。
出发去云南前夜,她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声音苍老,带着浓重西北口音:“你是林小禾吗?”
“是我,请问您……”
“我是那个寄手抄日记的人。”男人顿了顿,“我不是为了出名,也不是求什么回报。我只是……昨晚做了个梦。梦见我爹站在我床前,穿着破棉袄,浑身湿透。他说:‘儿啊,我把命都记下来了,你咋还不让人看?’”
林小禾握紧话筒,喉咙发紧。
“所以我打这个电话。”他说,“你能来一趟吗?就在青海湖西边的小县城。我家老屋还在,炕洞里还藏着三本我没抄完的账册??那是当年公社虚报产量的真实记录,连哪天杀了最后一只鸡都写着。”
“您叫什么名字?”她轻声问。
“张德海。”他缓缓道,“我爹叫张有田,是个会计。1961年冬天,他因为不肯改数字,被人绑在场院柱子上冻了一夜,第二天人没了,嘴还张着,像是要说什么。”
“我会去的。”林小禾说,“一定。”
挂断电话,她翻开行程表,在原定路线之外添上一笔:青海。
七日后,林小禾抵达云南山区。山路崎岖,汽车无法通行,她徒步两小时才到达杨素芬居住的寨子。老人住在吊脚楼里,背已驼,眼神却清亮。见到她第一句话便是:“你长得像你外公。”
林小禾怔住。
“三十年前他在这一带做过巡回讲师,讲民间文学。我听过他一次课,讲《诗经?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他说这不是打仗的悲壮,是普通人回不了家的痛。”老人说着,从柜底取出一只陶罐,“这是我哥哥的骨灰。我一直没敢撒,就想等一个人来,替他说句话。”
林小禾双膝落地,跪在老人面前。
她们谈了整整三天。林小禾用录音笔录下每一句话,也用手抄下那些无法录音的细节:哥哥如何在寒夜里为村民偷偷称量救济粮,如何把自家口粮分给孤儿寡母,又如何在被押走前夜,把日记塞进灶膛夹层。
第四天清晨,林小禾带着资料离开。临行前,杨素芬拉着她的手说:“我不求政府道歉,也不指望谁赔偿。我就想让我孙子知道,他爷爷不是坏人,是个好人,只是生错了时候。”
回到书院后,她将所有材料整理归档,并提交给“语音回溯系统”进行情感标记分析。结果令人震撼:在涉及“饥饿”“死亡”“冤屈”的叙述中,讲述者的声音频率普遍偏低,语速缓慢,常伴有长达数秒的停顿??那是记忆撕裂灵魂的间隙。
更惊人的是,在提及“孩子”时,几乎所有人的声线都会突然颤抖,甚至崩溃中断。系统标注为:**愧疚峰值区**。
苏晓看着数据图,喃喃道:“原来最深的伤,不是来自苦难本身,而是??我没能保护你免受我知道的痛苦。”
林小禾点头:“所以我们必须打破这种循环。不能再让父母对孩子说‘别问了’,不能再让孩子长大后才发现,自己家族的历史是一片空白。”
一个月后,诚言学堂推出特别项目:“家史工作坊”。邀请学生回家采访长辈,录制口述史,由学堂提供技术指导与保密支持。首批报名人数超过两千,覆盖全国二十三个省份。
一位内蒙古的高中生寄来回信:“我奶奶一辈子不说过去的事,每次问就说‘都过去了’。这次我拿出你们给的访谈提纲,她看了很久,忽然哭了。然后她讲了整整六个小时??关于她父亲被当作‘特务’枪决,关于她如何装疯逃过批斗,关于她藏在羊圈里的弟弟……她说:‘我以为这些事会跟我一起烂在土里,没想到还能说出口。’”
林小禾读完信,在日记本上写下:
>**语言一旦被囚禁太久,连释放它的人也会害怕自由。**
>
>**但我们仍要相信,只要有一盏灯亮起,就会有人鼓起勇气走向光。**
秋天来临之际,周明远再次启程,这次是赴青海。他拍下张德海老屋的照片:土墙斑驳,门框歪斜,炕洞里掏出的账册用油纸层层包裹,字迹虽淡,却清晰可辨。更有一页附图,竟是当年粮食分配路线图,红笔标注“领导专供”,蓝笔写“百姓定量减半”。
陈砚组织专家团队连夜核对,发现其中多个数据与地方志记载严重不符。更关键的是,这份账册能直接证明某位现已退休的省级干部曾在基层任职期间系统性贪污救灾粮。
消息尚未公开,压力先至。某匿名电话打到基金会办公室:“有些事,挖太深对谁都不好。”语气平静,却不容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