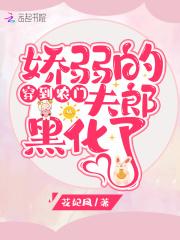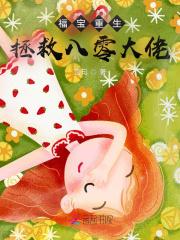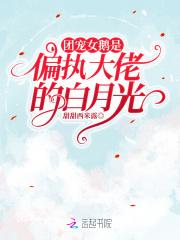笔趣阁>水浒开局在阳谷县当都头 > 第443章 臣罪该万死臣罪该万死(第1页)
第443章 臣罪该万死臣罪该万死(第1页)
政事堂内,诸衙议事。
程万里、宗泽、张叔夜坐头前,吴用、赵存诚坐后面,接着便是刑部御史台诸人……
今日何事,诸位自是都知,李纲也再重复说了一遍……
程万里皱着眉头,问了一语:“陛下之。。。
车队行至中牟,天色将暮。秋雨骤降,黄土路泥泞不堪,车轮深陷沟壑,马蹄打滑,寸步难行。三百师生披蓑戴笠,肩扛手推,衣衫尽湿,却无一人言退。篝火燃起时,已近子夜。沈小砚立于帐前,望着雨幕中模糊的山影,忽觉胸口一滞,喉间泛甜,一口鲜血喷在石上。
潘姓少女惊呼上前:“先生!”
他摆手止住,只道:“无妨。”随即盘膝而坐,从怀中取出陶罐,轻轻揭开封口。那一碗清水依旧澄澈如初,水面微颤,映出天上残月与火光交错之影。他凝视良久,低声道:“阿枝,你听得到吗?我们正走在你曾梦见过的路上。”
话音落处,水波轻漾,竟浮起一圈涟漪,仿佛有人在彼端轻轻点头。
次日清晨,雨歇云开,一道长虹横贯东方。众人整装再行,行不出十里,忽见前方官道中央立着一人。青袍素冠,手持竹杖,背对朝阳而立,身影修长如剑。
“是余仲衡!”有学子认出那人的面容。
沈小砚下马,缓步迎上。两人相距十步,彼此凝望。余仲衡终于开口,声音沙哑却清亮:“我来接你们入京。”
“朝廷允否?”沈小砚问。
余仲衡冷笑:“太庙三老自焚之后,玉玺已被禁军围守。当今圣上……已有半月未临朝矣。宫中传言,内廷已设‘静音局’,专查宫人言语,连梦话也要录报。守静者虽明面瓦解,暗里却仍盘根错节。”
沈小砚默然片刻,道:“那你为何敢来?”
“因为我已不是官。”余仲衡摘下乌纱,掷于泥中,“自昨日始,我辞去翰林编修之职,以布衣身份,奉诏??不,奉心而行。”
他转身指向北方:“补天军已破居庸关,韩定远亲率铁骑压境幽州。契丹旧部、渤海遗民、辽东猎户皆举旗响应。而南方七十二寨苗峒亦揭竿而起,打出‘问天’白旗。西北商路诸城闭门拒纳清心卫牒文,东南渔村私传《百无一用问录》,连佛门寺院也开始讲‘疑经’之课。”
他目光灼灼:“天下之势,非一人可挽,亦非一诏能定。但若你们进京,便是火种入殿。哪怕皇帝闭耳,你们也要让那些跪拜的臣子听见??人心,已经醒了。”
沈小砚点头,回身挥手。潘姓少女立刻命人打开一辆密封马车,抬出七具桐木箱。箱盖掀开,每一只都盛放着一卷古老竹简、一块刻满文字的石板,或是一册泛黄帛书??正是阳谷山腹所出的“未刊问典”。
“这一路北上,我们不再隐藏。”沈小砚朗声道,“每过一城,便开箱讲学一日;每经一县,便留书三册于学堂。我要让沿途百姓知道,百年来被抹去的疑问,并未真正消失。”
队伍再次启程。自此,每至一处驿站、集镇、书院,师生们便设坛开讲。有人诵读《问典》中失传已久的哲思片段:“子曰:君子不器。然今之为政者,欲使万民皆成无声之器,何其悖也?”有人演绎民间新问:“若雷公发怒必有因,那人间冤屈,谁来打闪?”更有孩童围坐,听老师讲述阿枝的故事,听完后仰头问道:“老师,我也能变成光吗?”
消息如风传遍九州。有些地方官惧祸不敢接待,却暗中派人抄录讲稿送往家中子弟研读;有些清心卫残余试图阻挠,派人在夜间纵火焚书,可第二天清晨,总有百姓自发聚集,在废墟之上重写问题,贴满城墙。
行至真定府,忽闻急报:汴京南门张贴皇榜,宣布三日后举行“大辩会”,由礼部主持,召集天下名儒、释道高僧、异术方士,共议“正道归一”之策。榜文称:“凡持异论者,许其登台陈词,以理服人。”
众人哗然。潘姓少女蹙眉:“此乃圈套。所谓‘以理服人’,实则设局诱捕。他们要当众驳倒你们,再以‘惑乱纲常’罪名治罪。”
沈小砚却笑:“正合我意。”
“先生?”
“他们终于肯让人说话了。”他眼中闪过锐光,“哪怕只是做戏,只要开了口,真相就有机会钻进去。我们要去,而且要堂堂正正地去。”
于是加快行程,昼夜兼程,终在辩会前一日抵达汴京城外。然而城门紧闭,守军宣称:“非持敕令者不得入内。”沈小砚正欲上前交涉,忽见城楼上一人探出身来,竟是昔日被贬岭南时结识的一位老驿丞。
“沈公莫慌!”那人压低声音喊道,“城中有变!昨夜宫中传出密令,要在辩会上启用‘忘音钟’??那是太祖年间铸造的法器,钟声一起,闻者心智蒙蔽,唯听诏谕是从!你们若贸然进城,只怕未及开口,便已失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