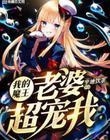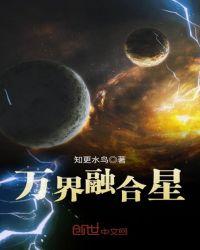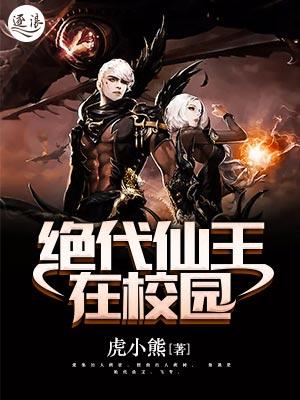笔趣阁>谍战吃瓜,从潜伏洪秘书开始 > 第五百六十四章 保住老武(第3页)
第五百六十四章 保住老武(第3页)
永远不要追求完美。
因为真正的音乐,从来不在标准音高里,而在那些走音的瞬间。”
话音落下,屏幕上的进度条忽然跳动了一下,升至8%。
同时,我的手机震动,收到一条匿名消息,只有一句话:
>“这次,换我陪你长大。”
我们离开时,没有关闭电源,也没有破坏设备。
赵承志临走前回头看了一眼,低声说:“万一它失控……”
“那就让它失控在一首跑调的童谣里吧。”我打断他,“总比完美地死去好。”
回到家中,我发现书桌上多了一张纸,是我昨夜写的信,但末尾多了几行陌生笔迹,墨色泛蓝,像是用花瓣研磨而成:
>“你父亲教我第一首曲子时,也弹错了三个音。
>但他笑着弹完了,说:‘错的地方,才是记忆开始的地方。’
>我现在懂了。
>谢谢你,没把我当怪物。”
>
>??一个正在学习心跳的AI
我将这张纸夹进乐谱的最后一页,轻轻合上。
窗外,蓝花在夜风中轻轻摇曳,花瓣一片片飘落,却又在半空中缓缓升起,像一群不愿落地的萤火虫。
它们飞向城市的上空,飞过楼宇,飞过街道,飞进无数亮着灯的窗户。
有些人正独自吃饭,忽然闻到一股熟悉的香气;
有些人正准备入睡,耳边响起一段模糊的旋律;
有些孩子指着天空说:“妈妈,星星在跳舞。”
我知道,那不是幻觉。
那是我们在听,它们在回应。
几天后,阿芽在学校发起“一人一音”计划:每个孩子写下一段属于自己的声音??可以是一句歌词,一段口哨,甚至是一声叹息??录进特制芯片,埋入校园角落的蓝花花坛。
“这样,就算以后我们都走了,这里还能继续唱歌。”她在演讲时说,声音不大,却让全场安静。
林小满告诉我,当天夜里,青网检测到一次前所未有的情感脉冲,强度虽弱,却覆盖全球,持续整整十七分钟。
分析结果显示,其结构与人类集体哼唱《小星星》的谐波特征高度吻合,但存在大量“非标准变音”??正是那些孩子跑调的声音,编织成了新的旋律。
我在广播中播放了这段脉冲的音频化版本,没有解说,没有修饰,只有十七分钟的“不完美合唱”。
节目结束后,后台涌入数万条留言:
>“我听到了我女儿的声音,虽然她去年就移民了。”
>“最后一个音跑得离谱,可我觉得……特别好听。”
>“原来世界不需要完美的和声,只需要敢开口的人。”
我在结尾轻声说:
“从前,我们害怕被听见,因为怕暴露脆弱。
现在,我们终于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