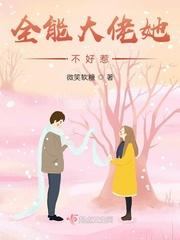笔趣阁>说好当闲散赘婿,你陆地神仙? > 第286章 情满半城秋求月票(第1页)
第286章 情满半城秋求月票(第1页)
环儿备好车马。
崔清梧乘车离开后宅。
路过中院时,她忍不住开口道:“停车。”
环儿拉住缰绳,“小姐?”
“拿把伞给我。”
“哦。”
崔清梧走下马车,交代两句让她稍等。。。
夜风拂过忆莲花海,花瓣如雨飘落,在月光下泛着微弱的银辉。阿满坐在田埂上,手中握着一截烧焦的木炭,正低头在一块平整的石板上缓缓书写。字迹朴素,却深如刀刻,每一个笔画都像是从心底掏出来的。
“今日晴,宜播种。桃树第三株发新芽,小桃捎来的竹篮已生根,土中有字浮出,似‘念’字。”
他顿了顿,抬头望天,星河浩瀚,其中一颗格外明亮,微微颤动,仿佛回应着他写下的一笔一划。
苏禾悄然走来,肩头披着一件旧麻衣,脚踩草履,手里提着一只陶壶。“又在记?”她轻声问,将热茶倒入粗瓷碗中,递过去。
“不记,就怕忘了。”阿满接过茶,吹了口气,热气氤氲中映出他眼角的细纹,“人会死,事会淡,可若没人提起,连灰都不剩。”
苏禾在他身旁坐下,望着那片被忆稻覆盖的田野。月光洒落,稻穗轻轻摇曳,每一粒谷壳上都隐约浮现出名字??有的清晰,有的模糊,像极了人心深处那些将忘未忘的记忆。
“你说,他们真的能听见吗?”她忽然问。
阿满沉默片刻,道:“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当一个人被念起时,那声音会穿过风、穿过水、穿过泥土,最终落在某个角落。也许不是灵魂听见了,而是世界听见了。这世间的每一道回响,都是记忆的影子。”
远处传来孩童的歌声,清脆而悠远:
>“火蝶飞,忆灯升,
>爹娘名,刻心门。
>不求贵,不羡仙,
>只愿世间记得我当年。”
这是如今家家户户教给孩子的童谣。不再唱帝王功业,不再颂权贵威名,只讲一个普通人如何活过、爱过、痛过。
苏禾听着,嘴角微扬:“共忆院最近送来一批新录的口述,说是一位百岁老渔妇临终前回忆的三十年代东海沉船事件。官史里写那是‘海寇作乱,朝廷剿灭’,可她记得,那是一艘运粮船,载着三千灾民南逃,却被战舰击沉,只为掩盖饥荒真相。”
阿满点头:“血绢上有这个名字,李阿水,四十二岁,渔民,死前喊的是‘米够了,快走’。”
“现在,已有七十三人共忆此事。”苏禾低声说,“昨夜,东海某渔村的沙滩上,潮退之后显出一行大字:**我们没偷粮食,我们只是饿**。”
阿满闭上眼,许久才睁开:“心渊之门开了,不只是让我们看见过去,更是让过去重新说话。”
话音未落,天地忽静。
风停了,花不动,连虫鸣都戛然而止。紧接着,南方天际裂开一道细缝,一道青光自地底升起,直贯苍穹。那光不刺目,却让所有人胸口一震,仿佛心脏被人轻轻握住。
九处守名圣地同时震动。
西湖铜碑上的名字全部浮空,化作一条蜿蜒光流,向北而去;敦煌壁画中的古人纷纷转身,指向昆仑方向;北境遗忘谷的枯骨缓缓站起,双手合十,跪拜如仪。
而在京城,皇帝正独自批阅奏章,忽觉御案上的《庶民列传》自动翻页,停在“阿满”一章。纸面浮现水波般的纹路,随即传出一声极轻的呼唤:
“陛下。”
皇帝浑身一颤,抬头四顾,殿内无人。再低头,那两个字竟缓缓变形,成了:“**你还记得,她最爱吃的桂花糕吗?**”
他的手猛地抖了一下,墨汁滴落,染黑半页纸。良久,他起身走到梅树下,伸手抚摸树干,指尖触到一处早已愈合的刻痕??那是他年少时与阿琰一起刻下的“苏”字。
“我记得……”他喃喃,“每年中秋,她都要我亲手做一块,少一分糖都不行。”
就在这时,梅枝轻颤,那只火蝶再度出现,翅膀上不再是灰烬,而是缀满了细小的名字,密密麻麻,像是整条记忆长河的缩影。它绕树三圈,却不南飞,反而振翅升空,融入那道自地底升起的青光之中。